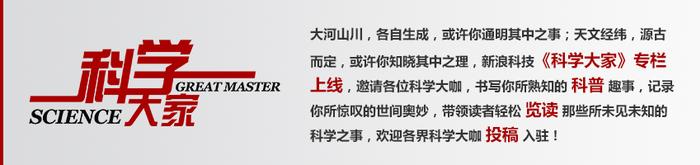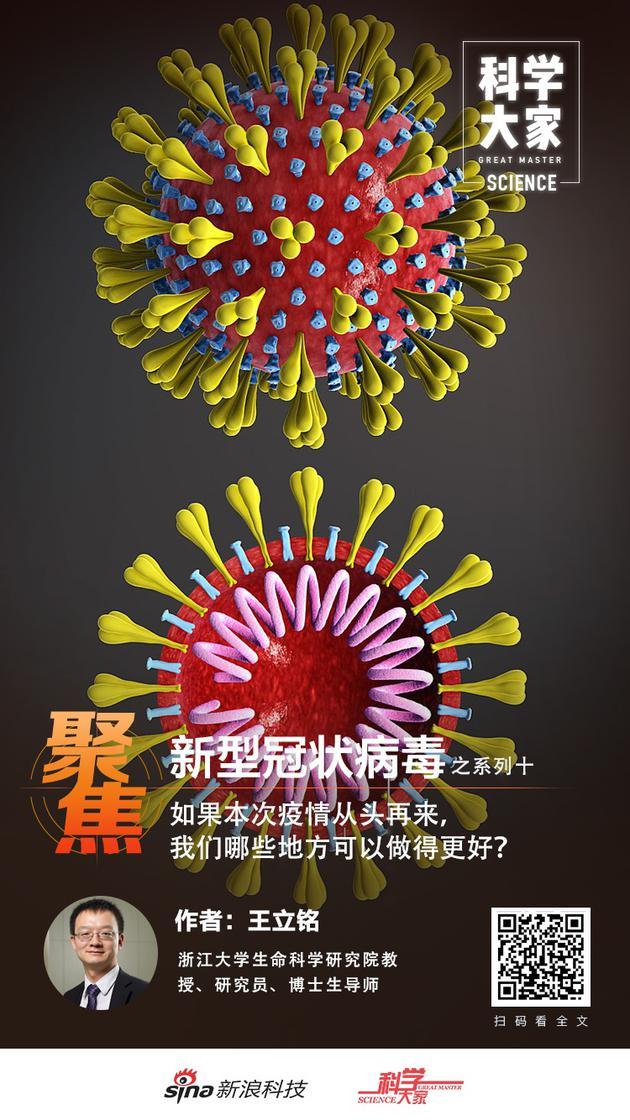
出品:新浪科技《科学大家》
撰文:王立铭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这几天,已经有很多媒体报道从各个角度、特别是一线医护人员的直观视角,总结过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出现的、特别是早期疾病发现和预警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我首先得强调一句:在疫情的危急时刻大家都希望听好消息、正能量,这个没错,我也一样。但是,这不意味着所有反思、批评和建议都是添乱、都是制造恐慌和焦虑。我更不觉得所有的反思、批评和建议都应该拖后,留到疫情结束再说。原因很简单,本次疫情还尚未结束(甚至还远未结束),在这场防控疫情的战争中,任何一点可能会优化效率、改善结果的东西,可能都对最后的结果非常关键。
本文的目的正是如此。
我会从现有的新冠肺炎相关文献展开分析,看看在对抗新冠肺炎的过程里,我们——也就是科学家群体——有哪些地方做的还不够好,在这次乃至未来的新发传染病疫情中,有改进的空间。
传染病防控是一个需要调动全社会资源的系统工程,其中科学在其中起的作用只是一小部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小部分)。我把它简单总结成四点:
• 在疾病出现的早期,及时发现疾病,特别是导致疾病的病原体,为此后的流行病学监测、疾病诊断和治疗提供支持;
• 在疾病出现的早期,快速和准确地判断疾病的危害性,特别是人际传播的能力,为此后的防控手段设计提供支持;
• 在疾病流行过程中,进行检测方法的开发,为防控疾病提供新的医学工具;
• 在疾病流行过程中,进行临床治疗手段的研究,为治疗疾病提供新的医学工具;
在这四个方面,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得更好?
我认为,都有。
先说第一个方面:及时发现疾病,特别是导致疾病的病原体。
在疾病的早期发现方面,我们已经做的非常出色。根据公开文献,第一例有据可查的新冠肺炎患者在2019年12月1日发病,截至2020年1月2日一共出现了41位确诊患者(Huang C et al Lancet 2020)。而在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张继先医生已经做出了“这是一种新型传染病”的判断并上报当地疾控部门(http://www.ccdi.gov.cn/lswh/renwu/202002/t20200207_210984.html)。考虑到冬季本身就是各种呼吸道疾病高发的季节,在武汉市内因发热咳嗽前往医院的患者可能多达每天数千人,在仅有几十例病患的时候就能做到准确判断和及时上报,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而在病原体发现方面其实动作也很快。
张继先医生已经率先排除了流感、腺病毒、合胞病毒等常见的呼吸道病原体的存在。而有证据显示,最晚在2019年12月底,我们已经在患者的下呼吸道样本中,通过高通量基因测序的方法,得到了新冠病毒的完整基因组序列,从技术上已经能够确认这种全新病原体的存在。
我这个判断,也可以从不同的公开信息中得到验证。根据新闻报道,武汉华大基因公司在12月底成为最早检测到新冠病毒的机构之一(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zw/sh/2020/01-28/9071974.shtml)。而国家疾控中心也在2020/1/3的例行周报里,公布了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全长序列(http://weekly.chinacdc.cn/en/article/id/a3907201-f64f-4154-a19e-4253b453d10c)。另外,在2020年1月2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已经能够根据病毒的核酸序列,对59位疑似患者进行筛查,并确认了41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Huang C et al Lancet 2020)。
如果考虑到全新病毒的基因序列拼接和分析是一个需要不少时间的、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在12月底,在临床医生们汇报新发传染病之后不久,中国科学家们已经能够锁定新冠病毒这种全新的病原体了。
这是个非常惊人的速度,和SARS时代对比,我们发现新病原体的速度快了很多倍。
但是,从公开新闻中你也会发现,政府有关部门正式公开新冠病毒的消息,是在1月9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01/1048911)。
因此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是,从技术上能够确认新冠病毒,到正式发布消息,至少有10天的滞后期。这是为什么?
请注意,我不是要试图提出指责,因为这个滞后时间在科学层面上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的原因是,在科学上,从患者的体内检测出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的存在,和能够确凿的判断这种冠状病毒就是患者得病的原因,其实不是一回事。
你应该能够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每个健康人体内都携带着大量不同的微生物,但是它们绝大多数都和人体和平相处不会引发疾病。我们不可能因为检测到一个新的病毒,就能立即断定它就是疾病的罪魁祸首。
而如何判断一种传染病的病原体,其实有一个非常古老但行之有效的办法:科赫法则。

这是德国细菌学家科赫在1884年提出的标准,用来判断某种病原体和某个传染病之间的因果关系:
• 每一个病患体内都能找到大量的这种病原体;
• 这种病原体可以从患者体内被分离出来,然后在体外培养;
• 体外培养的病原体可以让健康人患病;
• 新患病的人体内仍然可以找到同样的病原体。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科赫法则也在持续地被修正过程中,但是总体而言仍然是整个科学界明确传染病病原体的金标准。
但是请注意,除了科赫法则1相对可以快捷的完成——只需要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患者的组织样本进行检测和序列分析——之外,后面几个步骤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实验验证。实际上有些步骤至今仍然没有彻底完成,比如说我们尚未看到报道说在患者的尸检中确认了新冠病毒的存在(科赫法则2),我们也还远没有建立新冠病毒的动物模型,用来直接验证科赫法则3和4(当然有一些间接证据,Zhou P et al Nature 2020)。
因此,从科学角度说,为了准备更充分的证据,10天的滞后发布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事后反思的话,这段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呢?毕竟,在疾病爆发初期的10天可能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多,如果能够提前10天预警新冠病毒的存在,那么防控疾病的行动也可以更早开展、更有针对性。
我认为是可以的。
这里是我的建议:在基因组学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的现在,我们有能力在科赫法则尚未完全得到验证之前、尽早对新病原体提出预警。
理由是这样的:应用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我们能够快速地在患者组织样本中筛查大量的已知病原体、发现新病原体。如果在疾病出现的早期,在不同患者体内检测到同一种病原体的出现、而这种病原体在健康人中并不存在,同时这种病原体可能和医生们观察到的疾病症状有关,就已经能够清晰地提出预警信号了。特别是考虑到曾经在人体中被发现的冠状病毒(一共有7种,包括SARS和MERS)无一例外地都引起了人类呼吸道疾病,而且都有人际传播的能力,这种早期预警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因此,在基因组学技术广泛应用于临床检验的时代里,我们完全有可能在科赫法则被完全验证之前,发现新病原体,并提出早期预警。请注意,科学结论固然需要尽可能的严谨,但是涉及到疾病快速响应和公共管理政策的调整,如果固守陈规,则可能会太过保守,从而错失疾病管控的黄金时间。这一点,在最近疾控中心领导的访谈中也有所体现(http://www.bjnews.com.cn/news/2020/01/31/682224.html)。
再说第二个方面:预测疾病的危害性,特别是人际传播的能力。
病毒人传人的能力涉及到对传染病严重程度的根本判断。道理很简单,如果病毒只能从宿主动物传播到人,那么只需要清理宿主动物(比如关闭海鲜市场)就可以彻底扫清疾病;而如果病毒具备了人际传播的能力,那么防控压力会骤然增大。
这也是本次疫情中屡屡被讨论的话题。在这里,我们仍然仅从科学角度加以分析。
从已有的科学文献分析,我们是什么时候获得人传人的直接证据的?
我认为是2020年1月上旬。
理由如下。
在12月底到1月初;出现了几起家庭聚集性感染的案例(Li Q et al NEJM 2020)。比如说有这么一个案例:12月20日,有一位61岁的男性(曾某某)开始发病,并于27日入院。他的两位家庭成员(应该是妻子和女儿)也分别在25日和29日发病。值得注意的是,曾某某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但是他的两位家庭成员却并未去过海鲜市场(Li Q et al NEJM 2020, Huang C et al Lancet 2020)。考虑到发病-入院-确诊的时间窗(大约10天左右),那么在1月上旬,新冠病毒人传人的迹象已经相当明显。
类似的证据还有,在1月10日前后,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收治了六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他们是一个家庭的成员,此前刚刚从武汉返回深圳。而1月15日,该家庭中一位并未前往武汉的成员也开始发病入院接受治疗。尽管在此时香港的研究者们还无法100%确认这种疾病就是新冠肺炎(因为没有做核酸检测),但是这种疾病人际传播的证据也已经很充分了 (Chan JFW et al Lancet 2020)。
再有,截至1月11日,有7名医护人员被感染。这同样是非常明确的疾病人际传播的证据(Li Q et al NEJM 2020)。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推断,在1月上旬,支持疾病人际传播的证据已经相当明确,而且来自不同的渠道,可信度很高。
但是,从公开新闻中你也会发现,新冠病毒人际传播的消息,是到了1月20日才由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宣布的(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1/20/c_1125487200.htm)。
因此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是,从医学上能够确认人传人,到正式发布消息,仍然有10天的滞后期。这是为什么?
请注意,我仍然不是要试图提出指责,这个滞后时间固然可能是重大疏失,但在科学层面上仍然不是不能理解的。
传统上,一种疾病是否出现人际传播,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流行病学调查。就如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些家庭成员患病的例子一样,研究者们需要考察每一位患者在发病前的生活轨迹——去过哪里、干了什么、和谁接触过——然后判断疾病的传播路径。但是你可想而知,这种调查出错的可能性很大,毕竟人类的记忆是很容易失真和被扭曲的,更不要说还可能存在故意欺瞒的情形。既然如此,流行病学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是流行病学的数据经常需要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被充分信任。而反过来说,病毒能不能人际传播,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却是极其重大的。
用较为不可靠的数据作出重大决定,这本身就很不容易。
因此,尽管我们事后去看,病毒人际传播的迹象很早就非常明确,但是我也能够理解决策者可能需要更多、更多的证据、更长的时间,才能下这个决心。很难说这种等待是有意拖延还是力求谨慎,但是科学证据本身的薄弱显然大大加剧了下决心的难度。
我们事后反思的话,这段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呢?毕竟,如果能够提前10天预警新冠肺炎的人际传播,那么我们可以更早地切断公共运输,限制疾病的扩散,我们也能够避免诸如万家宴、团拜会这样的聚集性活动。
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这里我提出两个可能性:
一个可能是,也许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人际传播“的定义,尽可能地去掉模糊空间,让临床医生、决策者和老百姓都能够真正明白在什么时候可以做出如此判断、何种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规定,当第X个聚集性发病出现,或者当第Y位医护人员被感染出现之后,就应该提出”人际传播“的预警,在公共管理方面开始采取措施了?当然,X/Y的具体数值需要谨慎的设计,防止太效以至于经常误发警报,也要防止太大失去了预警的价值。
除此之外,像”不排除有人际传播的可能“,”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等科学存在不同的解读空间,但是在公共管理层面很容易引发误解的概念,应该尽量避免使用。
另一个可能是,我们仍然可以借助基因组学等新技术,在传统的流行病学研究之外,为”人际传播“提供更坚实的证据。
刚才我们说到,基因测序技术可以帮助我们部分的绕过科赫法则,提前预警新病原体。我们也提到了,鉴于所有的七种人体冠状病毒都可以人际传播,实际上基因测序技术可以在更早的时间帮助我们预警新冠病毒的传播能力。
更进一步,基因测序技术还能够对比不同患者之间病原体基因序列的差别,判断出这种病原体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情况。通俗的说,病毒在传播过程中在不断地发生基因变异,可能每传播一次都会出现一些新的基因变异,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测出基因变异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回头描绘出这种病毒的传播路径。
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过一家三口都得上了新冠病毒肺炎。如果通过基因测序,发现他们三者的基因序列高度类似,但都和其他患者有些差异,这个发现结合流行病学的调查,就可以更好的判断你,病毒在这些家庭成员之间有传播。
最后,我来简单总结一下。
用后视镜视角,从公开数据出发,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当中,我们其实是有可能争取到10天甚至更多的时间,提前对新病毒、对人际传播能力做出预警,从而更好的防控疫情的。当真如此,整个防控局面可能会大有不同。一个很好的参照对象是这次疫情里香港的反应。香港当局早在12月底就开始评估疾病情况,在1月头几天就启动了相当严格的疾病管控措施(包括对武汉方向旅客的筛查),也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当然,在真实历史中进行决策显然没有那么容易,可能也不能过分苛求。
在这里,我不想对任何人提出指责,但是我希望,这些反思和建议,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这次疫情,还有以后可能会出现的新发传染病。
好,我们现在继续讨论后两个部分,疾病诊断和治疗手段。
第三,疾病诊断方法的开发,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我认为也是有的。
我们先说检测方法,根据国家卫健委2/4日发布的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对新冠肺炎的诊断主要包括三个因素:流行病学史(通俗的说就是是不是去过武汉、接触过其他病人等等);临床表现(发热、肺部CT指标、白细胞正常或降低等指标);以及检测到病毒的存在(PCR方法或者病毒基因测序方法)。(http://www.nhc.gov.cn/yzygj/s7653p/202002/3b09b894ac9b4204a79db5b8912d4440.shtml)
其中可能特别值得讨论的是最后一点:病原体检测。
咱们在上面讨论过,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科学家们在很短时间内锁定了新冠病毒这种全新病原体,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这个发现却可能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因为确定了新病原体的存在,因此对新冠肺炎的确诊就必须要求病原体检测结果阳性才可以(参考卫健委诊疗方案第一至第五版)。
这件事从理论上说当然是非常有道理的:既然新冠肺炎的病原体已知,同时临床症状又相对不是那么典型(不太容易和其他呼吸道疾病区分),那么借助最新的科学发现,利用PCR或者基因测序的方法明确病原体的存在,再做出确诊当然是个很稳妥的办法。
但是问题在于,利用PCR方法检测病原体,传统上就是一个特异性不错、但是敏感度不高的方法——通俗的说,就是如果测出来阳性那基本上就是有病毒,但是很多患者明明有病毒就是测不出来。我们用流感病毒的检测来做个类比,它的特异性有90-95%,但是敏感度只有50-70%(https://www.cdc.gov/flu/professionals/diagnosis/overview-testing-methods.htm)。换句话说,可能只有一半多的患者能够通过PCR检测得到确诊。(而基因测序又因为样本和成本原因没法大规模开展。)
从公开报道来看,这个问题在新冠肺炎的检测中也存在,甚至还更严重(http://www.caixin.com/2020-02-07/101512517.html),而且可能还产生了双重的负面影响:
一方面,如果无法通过PCR检测,患者无法正式确诊,也就无法纳入正式统计数字当中,治疗也可能会受到影响(这点可以参考财新杂志的报道:http://china.caixin.com/2020-02-05/101511802.html);另一方面,即便是结果比较一般的PCR检测,也大大受限于检测试剂盒的生产和供应能力,以及不同厂家的试剂盒的层次不齐的质量。实际上我们从新闻中屡次看到核酸检测阴性的患者,其实他们可能主要是因为PCR检测本身的问题导致的。
如果说在前面两个部分,我在强调我们应该用最新科技——特别是基因组技术——加快疾病的预警,那么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应该在另一些场合主动抛弃技术的约束。
简单来说,就是不能让病毒的(较为不可靠的)核酸检测,成为约束疾病准确诊断和治疗的因素。
这一点其实在最新诊疗方案中已经有所体现。针对湖北省内的患者,增加了“临床诊断”病例这个分类,专门用来描述流行病学史和临床症状符合新冠肺炎定义,特别是肺部CT有明确证据,但是病毒检测阴性的患者。我想也许伴随着更多的证据,这一条值得逐渐推广到其他各个省份,防止因为核酸检测本身的问题耽误治疗。
与此同时,更灵敏的病毒检测技术的开发也需要加速。传统上,在PCR检测之外,基于抗体的检测方法要更加灵敏(也更加快捷),这在未来将会是非常重要的诊断工具——特别考虑到武汉地区、乃至整个国家可能都需要长期和全面地进行疾病筛查。同时,也有更多的病原体检测技术值得探索,包括基于基因编辑技术的快速病原体检测等等。
第四,临床治疗手段的开发,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也有。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件事,针对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疾病,临床上并没有什么特效药可以立竿见影——这一点不光对于新冠肺炎适用,对于SARS,对于流感引起的疾病也都是如此。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对抗病毒,特效药本身并不是必须的,临床医生们传统上利用高强度的支持治疗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通俗的说,就是通过辅助呼吸、抗感染、补充体液等方法维持患者的生存,然后等待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消灭入侵的病毒。
当然了,即便如此,大家肯定都还是非常期待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能够对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帮助我们对抗疾病。这样的药物当然也会大大减轻人们的恐慌情绪。
但是我必须得说,在这个方面,科学家们的作为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已经反复强调,在疫情爆发的短时间内指望开发出全新的药物技术上就是做不到的——这违背了药物开发的基本规律。所以这段世界里,科学界的关注焦点是“老药新用”,也就是看看市场上已经广泛使用的药物(不管他们本来针对的是什么疾病),有没有可能移花接木用来治疗新冠肺炎。
在过去这几周,有这么几个“老药新用”的案例被广为传播,相信你也看到了。
• 一个是在北大医院王广发主任的案例里被发掘出来的艾滋病药物克立芝(洛匹那韦/利托那韦)(https://new.qq.com/omn/20200126/20200126A0H45F00.html);
• 还有一个是应用在美国第一个新冠肺炎患者上的埃博拉药物瑞德西韦(Holshue ML et al NEJM 2020)。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新闻里提到了不少别的老药也许也可以用于新冠肺炎的治疗,比如抗病毒药物阿比朵尔和艾滋病药物达芦那韦(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0/2/435381.shtm),甚至还包括了常用药沐舒坦(https://tech.sina.cn/d/bk/2020-01-29/detail-iihnzahk6887090.d.html)和双黄连(http://www.cas.cn/yw/202001/t20200131_4733137.shtml)。
对于这个现象,我认为科学家们需要非常谨慎:不管是开展研究、还是诉诸舆论。
原因很简单,药物开发有自己的基本规律。对于任何一种药物来说,在真正大范围的向患者群体推广之前,必要的验证工作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这既包括在实验室内进行的关于药物作用机理方面的研究(所谓“临床前研究”),也包括在一部分患者群体内进行人体的临床试验。这些研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潜在药物的作用机理、安全性、药效,使用方式和使用范围。
也就是说,哪怕是一款老药、一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确实比较安全的老药,也不应该在没有充足证据之前贸然推广。
但是目前所见,有些科学研究的方向和发布方式是明显违背了这些基本规律的。比如说克立芝,这种艾滋病药物因为北大医院王广发主任使用后病情好转,很快被公众所熟悉。但是他们很可能并不知道的是,这种药物到底能不能治疗新冠病毒肺炎,目前的证据是极其有限的!它这次被拿出来用,唯一的可能依据是,2004年香港学者在SARS期间在四十几位患者中尝试了这种药物,事后发现效果还不错,降低了死亡风险(Chu CM et al Thorax 2004)。但是即便是这项研究本身也有不少科学家提出了严肃的质疑(Stockman LJ et al PLoS Med 2006)。而它对这次的全新病毒是不是管用,目前还没有任何人体临床数据支持。相反,即便在小规模的尝试中医生们也观察到了不少严重的副作用,比如心脏不良反应、胃肠道反应、血糖异常、胰腺炎、血脂升高、肝损伤等问题。考虑到这次不少重症患者本身就携带很多基础的代谢和心脑血管疾病,这些副作用就更加值得警惕了。
但是值得思考的是,正在全面验证克立芝药效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一项评价洛匹那韦利托那韦联合标准治疗在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住院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随机、开放、对照的研究),克立芝这种药物已经正式进入了卫健委的诊疗方案当中。
这是不是有可以商榷之处呢?
类似的例子还有瑞德西韦。
这种药物因为被用于美国第一个新冠肺炎患者而被公众熟知(Holshue ML et al NEJM 2020),国内研究机构也证明了这种药物在体外的病毒抑制效果(Wang M et al Cell Research 2020)。但是和克立芝类似的是,这种药物的真实疗效和安全性刚刚开始测试(瑞德西韦治疗2019-nCoV感染患者的疗效安全性研究),但是各种宣称它神奇疗效的文章就已经开始遍及互联网,甚至有人还把这种药物应景的翻译成了“人民的希望”(remdesivir)。
毫无疑问,老药新用,确实是应对新发传染病一种比较现实的方式。如果克立之和瑞德西韦这样的药物能在短时间内证明自己的疗效和安全性,无疑会大大丰富临床一线对抗新冠肺炎的工具库。除了这两个药物,中国科学家也应该继续投入更多的老药新用的研究中,看看更多的老药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对抗新冠肺炎。考虑到很多抗病毒药物的广谱性,这个期望应该不是天方夜谭。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不顾药物开发的基本规律,随意的将非常初步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体外研究成果)公诸舆论、将尚无明确证据的药物广泛应用甚至写入指南,这本身导致的问题可能还要超过潜在的价值。
这一点,也许在对抗新冠肺炎的未来战场上,仍然需要我们反复提醒自己。
好了,在这里也简单总结一下三四部分的内容。在疾病开始流行之后,开发更好更多的疾病诊断工具,将更多的好药推向临床一线,同样是科学家们的职责。同样从后视镜视角,这两个方面,我们仍然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面向未来,在正在进行的对抗新冠肺炎的战场上,我们有可能做的更好。
而在更长远的未来,在疾病流行过程中、乃至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在新冠肺炎销声匿迹之后,我们仍然应该继续投入于疾病的基础研究、药物开发和疫苗研制,为这种疾病的长期流行或者重新流行做好准备。也许到了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工作将远离公众关注,也享受不到多少鲜花和掌声,但是它们,同样是科学家们的神圣职责。
特别是考虑到我在上一篇文章里的一个猜测,那就是新冠病毒的流行,因为庞大的患者基数和较强的隐匿性这两个大麻烦,使得类似SARS时期的战时措施,可能很难一蹴而就地彻底消灭病毒,我们也许不得不接受这种“大号流感”的长期存在,甚至需要因此调整防控疾病的策略。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我在本文中总结的这些经验和教训,如何与时俱进地使用新技术加快疾病的诊疗、如何同时防止新技术对诊疗的干扰、如何开发更有效的诊断试剂、药物和疫苗,也许,能在对抗新冠病毒的长期战争中起到作用。
推荐
《科学大家》专栏投稿邮箱:sciencetougao@sina.com 来稿请注明姓名、单位、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