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重版权固然必要,但如果高高矗立在知识与公众之间的付费墙成了商家的摇钱树,则知识产权保护也失去了其“保护知识”的意义,造成知识与财富的双重垄断。
过去这个春节,或许是中国普通民众和学术走得最近的一段时光。
武汉P4病毒实验室、特效药、临床试验、超级传播者……各种名词满天飞,人们匆匆打开电脑,不管能不能看懂,先下载一批相关论文再说。
于是,去年备受关注的知网再一次登上热搜。
不久前,几个学术资源数据库用实际行动支持抗疫,放出了“免费”的消息。只是,这则喜讯在短暂刷屏后又马上被辟谣——维普确实是提供论文免费下载了,但知网提供的所谓免费服务却是另有所指。

二月初,知网因此前的免费公告引发读者误解而发布说明并致歉。其中明确,知网在疫情期间提供的免费服务项目是指高校及职教用户校外漫游服务、OKMS·汇智系统以及知网研学三项。
其中OKMS·汇智提供的是机构的在线协同研究、协同管理服务,知网研学则是用于文献检索、笔记、思维导图等的学习平台。
翻译一下,这三个免费项目中,唯一和“免费读论文“挂得上钩的,是知网研学提供的免费服务中,包括一项HTML碎片化内容阅读,限每人每天可在线阅读文献不多于20篇。
简言之,这次知网发的免费福利主要是一个办公系统和一个学习平台,而看论文该花的钱,还是得花。
人们得知“被骗”时有多愤懑,恰恰说明了对免费的盼望有多迫切。从科研人员到普通学生,从翟天临到老百姓,天下苦知网久矣。

不少网友晒图显示所需内容并非免费。
一、重回千古之问:“知网是什么?”
整整一年前,一句“知网是什么东西”的天真发问掀开了高校学术作风问题的遮羞布。问题被挂着博士头衔的翟天临念出来,变成了年度翻车现场。
“无知网不论文”,几乎已经是当代大学生的基本认知。作为论文选题的灵感库,材料研究的素材集,懂得怎么遨游知网,是学术小白迈入新世界的必备素质。
中国的学术资源数据库,当然不止知网一家。除了这次实打实发了免费福利的维普中国期刊,另外还有万方数据库、超星、读秀等等。而其中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还是要数知网。
诞生于1999年6月的中国知网,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建立,是中国知识基础设施(CNKI)工程的服务网站,被定位为“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的的信息化建设项目”。

知网界面,免费说明已经出现在醒目处。
但CNKI最早的产品并非网站,而是光盘。20世纪90年代初期,正值计算机技术方兴未艾,CD光盘是当时最普遍的数据存储工具。
1992年,国内第一张CD多媒体光盘出版。一年后,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重庆分所实现了在CD光盘上进行文献题录检索的功能。
但当时的技术仍有缺陷,使用者在使用光盘检索后,还需要通过纸本资源获取一次文献。解决这一问题的人,正是CNKI创始人王明亮。
1995年,他提出“版面显示+全文检索技术”,不仅可以检索出题录摘要,还能够直接查看期刊全文。同时,以CD光盘为载体的数字资源基本实现了与纸本期刊同步出版。

曾经的开创性产品CAJ,如今被不少人视为鸡肋。/孔夫子旧书网
这一划时代的产品被称为“CAJ-CD”,一张薄薄的光盘,正式标志着中国迈入数字图书馆时代,也成为知网诞生的前奏。而今我们所说的“中国知网”,就是CNKI开始向互联网转型后的研发产品。
和三大数据库中的另外两家——维普和万方相比,知网对核心期刊、工具书的收录范围最为全面,还有独家的硕博论文数据库,其查重服务也涵盖了期刊发表、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生毕业论文等各种类型——当然,这都是需要付费的。
三足鼎立的格局下,对普通大学生来说,往往有一个知网就足够了。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地位,知网的傲慢也与日俱增。

知网三大刊物曾被作为国礼赠予伊朗总统。
二、知网生意经:写论文不赚钱,但囤论文赚钱啊
知网到底是怎么赚钱的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资源这本生意经几乎不被大众关注。直到翟博士惊天一问,把自己和翟天临都带进了坑里。
中国最早的数据库建设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主要以地方图书馆资源的数据化为主。而数据库商品化和产业化,则是90年代后期开始的。
从2015年的15.84亿元到2018年的21.38亿元,互联网期刊出版行业的规模也逐年扩大。
去年,和众多学术不端事件一起被拉到聚光灯下的,还有知网的如意算盘。
根据同方股份年报显示,知网2017年度营业收入达到9.7亿元,毛利率61.23%。利润背后,是普通用户糟糕的使用体验,和知网十足难看的吃相。

此前,因为涨价幅度每年都在10%以上,诸多高校都对中国知网叫苦不迭。
早在2013年,由于涨价过高,云南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旗下所属的近10所省属重点高校就宣布停用知网;
2016年1月,武汉理工大学因续订价格上涨而发布停用通知;
2016年3月,北京大学官网上发布了正与知网进行2016年续订谈判的公告,原因同样是知网节节攀升的开价。

太原理工大学的相关公告。
售价这么高,那知网的商品——学术资源,又是从何而来呢?
新京报曾有报道,按照中国知网的稿酬支付标准,博士论文著作权人每篇论文可获得面值为400元的“CNKI网络数据库通用检索阅读卡”和100元现金稿酬;硕士论文著作权人则是300元的阅读卡和60元现金稿酬。
而这些用阅读卡和低微的现金稿酬买来的论文,放到知网上就是妥妥的摇钱树。期刊全文计费0.5元/页,硕士学位论文15元/本,博士学位论文25元/本,而知网的年下载文献总量,为20亿篇次。

知网收费明细。
且不说一篇博士论文付出的辛苦和一百块是否对等,但是这种用更多知网论文来换一篇论文的做法,就足够鸡贼。一手“低买”,一手“高卖”,构成了知网的盈利模式。
当人们终于开始认真审视知网,才发现这家学术网站已经闷声发大财这么久。但无奈的是,知网必须被我们“原谅”,正如当初和其闹掰的众多高校,最后也大都不得不坐下来再谈条件。
没奈何,在国内,只要论文还得写,知网就必须得用。所谓“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垄断学术资源的知网,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知网将充值金额设置为50元起,即便被起诉也不觉得有问题。
三、学术垄断,谁也绕不过去的坑
面对争议和指责,知网负责人曾在采访中作出解释:对于知网来说,版权成本是“大头”,包括许多知网独家资源和高成本的外文资料,“好的期刊资源价格也上涨了,加上公司的其他成本,我们的报价也就随之上涨”。
也就是说,虽然知网在支付论文稿酬上给自己省了一大笔,但“囤论文”的成本却依然省不下来。
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知网已与60多个国家地区700余家出版机构达成版权合作,收录外文期刊7万余种,图书81万余种,共计2亿多篇外文文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与海外交流逐渐密切的同时,知网也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国际 “产业链”之中。

知网达成合作的国际学术资源。
纵观全球的学术出版现状,“寡头垄断”也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市场份额一直向头部聚集。
目前,Reed-Elsevier(爱思唯尔), Tylor & Francis(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 Wiley Blackwell(威利-布莱克威), Springer-Nature(施普林格·自然)和Sage,五家出版公司掌握着全球一半以上的出版期刊文章。

爱思唯尔办公区。/爱思唯尔官网
而这些国际上的学术出版寡头身边,同样上演着高校控诉的桥段。2019年2月28日,由于合同谈判破裂,加州大学单方面宣布将暂停与爱思唯尔的合作,以抗议其高昂的订阅费用。
在此之前,加州大学系统每年至少要向爱思唯尔支付1100万美元。但交得多还不是关键问题,问题是交得亏——
在爱思唯尔收取的费用中,一部分属于“订阅费”,即交了钱之后就可以阅读文章;而另一部分是“文章处理费”,是指把文章放到网上、提供访问入口的费用。这就相当于买一份论文,得交两次钱。
加州大学提出要取消订阅费,只交文章处理费用,但被爱思唯尔集团断然拒绝。8个月的拉锯战后,加州大学正式退订爱思唯尔旗下期刊,并免费向全世界研究者提供加州大学的所有论文。
2014年,德国康斯坦茨大学(University of Konstanz)也因为爱思唯尔订阅价格在5年里增长了30%的惊人报价,全面停止订阅爱思唯尔学刊。
2018年,瑞典和匈牙利的许多大学也跟随德国同行的步伐,相继不再与爱思唯尔续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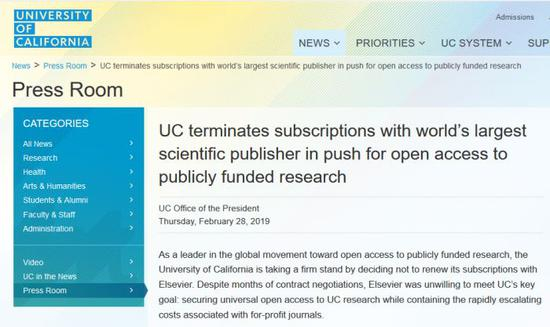
加州大学的声明。
而另一边,论文作者作为这些出版集团的“供应方”也提出了抗议。
2012年,著名英国数学家Timothy Gowers曾在博文中向全球科学界发出号召,集体抵制爱思唯尔出版集团。
原因是Gowers教授认为,这家旗下坐拥《柳叶刀》《四面体》《细胞》等知名学术期刊的出版集团正在无偿取得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以及评议工作,而刊登论文的期刊却一再涨价。
这种与中国知网 “高卖低买”如出一辙的行为,来源于出版社盈利至上的商业模式:
目前,科学家的实验项目开展大多由政府出资,作为其研究成果的论文则是免费提供给出版商,出版商再付钱给科学编辑,让他们判断作品是否值得发表、检查语法问题。
然而,这个“判断”工作实际上大多并不需要科学编辑负责。“是否值得发表”的标准是论文的科学有效性,这往往是通过“同行评议”来决定,而这一过程主要是由科学家志愿完成的。
所以结果就是,科学家们提供了科研成果和评议结论,而出版商依然是只需支付微薄的成本就可坐享其成。

堪称“知识界的海啸”。
无论国内外,出版商作为“中间商”赚差价的行为都如出一辙。普通人骂归骂,在这样坚固而庞大的商业链条面前,也只能萌生无穷无尽的无力感。
四、没有人能够阻挡,我对知识的向往
不是没有人试图改变这一局面。
面对寡头出版集团的强势垄断,少数自身实力过硬的学术机构可以通过退订抵制,而对于个体而言,转向盗版,几乎是一种必然会产生的选择。
盗版资源网站应运而生,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Sci-Hub。2011年,哈萨克斯坦神经学家Alexandra Elbakyan创立了这个能够提供多学科论文的资源网站。
在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网站将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自然等多家大型出版商旗下的期刊文章都收入囊中。有人甚至指出,几乎可以说99%的付费文章都能在Sci-Hub里下载到。

Sci-Hub官网。
在违法的边缘如此胆大妄为地试探,Sci-Hub在造福广大研究者的同时也注定要陷入长久的麻烦。
2015年,网站创办人Elbakyan收到了来自爱思唯尔的诉讼通知,纽约联邦法院最终裁定侵犯版权,要求其关闭在美国的服务器。
这场官司的确让Sci-Hub不得不频繁更换网址,和执法机关“躲猫猫”,但它也使Sci-Hub从此名声大噪,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盗版学术资源网站。
尤其讽刺的是,据媒体报道,在Sci-Hub收到的文献下载请求中,有四分之一来自经合组织的34个成员国——那些理应最易获取文献的富有国家;而出版业大寡头扎堆的美国,则是Sci-Hub文章的第五大下载国。
可见,有钱是一回事,但当午餐的价格贵得离谱,免费午餐的诱惑就会直线上升。
和出版集团的游击战打了这么多年,Sci-Hub总归是在躲躲闪闪的日常里勉强存活了下来。

创始人亚历山德拉·埃尔巴金,也曾饱受“高价知识”之苦。/wiki
而另一边,在加州大学系统作出与爱思唯尔“断交”的惊人之举后,学术界和出版界也更加意识到促进学术资源自由传播、拆除阻挡知识交流之墙的重要性,推动“开放获取”(Open Access,简称OA)越来越成为大势所趋。
在这种新模式下,作者付费出版自己的论文并保留论文版权,而读者无需再向出版社付费便可以查阅论文全文,大大推动了科研成果在互联网平台上的自由传播。
2012年7月6日,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了名为《数学论坛》(Forum of Mathematics)的OA期刊,并决定在该期刊发行的最初三年放弃出版盈利,向论文作者提供期刊全部文章的获取权。
2014年12月,《自然》出版者集团宣布将开放旗下40余种杂志的研究论文供读者阅读,但并不能免费复制、打印或下载。这种半开放相比起过去,无疑已经是巨大的进步。
就在刚刚过去的2月18日,继2014年全球排名第三的多学科类期刊《自然通讯》成为“开放获取”期刊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再次推出了《通讯-材料》《通讯-地球与环境》两本OA期刊,在推动“开放获取”的进程上显得诚意满满。

为抗击疫病,越来越多的知识平台打开了大门。
而在世界同行持续变革和国内用户不断批评的双重压力下,知网也试探着在开放获取上迈出了一小步。
在不久前的解释中,除了疫情相关,知网还列举了三项长期免费项目。
就2020年度而言,根据知网目前提供的免费服务,注册用户可以免费获取1911年-2011年间共11402种期刊出版的文献4089万篇,约占全部期刊文献的59.8%,另外还有同时段出版的硕博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
而面向作者的免费服务则是一项开始于2019年9月的新规定,作者可以免费浏览、下载知网所收录的该作者在国内以及在国外OA期刊发表的全部论文全文,曾经一度被调侃的“作者上知网下载自己的论文还要给钱”的情况将不复存在。
毕竟,知识最大的意义之一正是在于传播。
尊重版权固然必要,但如果高高矗立在知识与公众之间的付费墙成了商家的摇钱树,则知识产权保护也失去了其“保护知识”的意义,造成知识与财富的双重垄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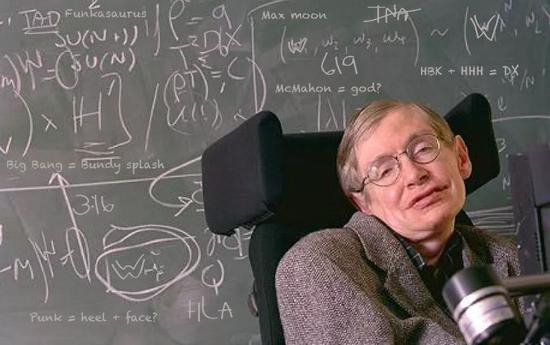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身体力行支持知识共享。
2017年10月,在剑桥大学网络资源“开放获取周”活动中,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将自己24岁时撰写的博士论文《膨胀宇宙的属性》(Properties of Expanding Universes)发布到了剑桥大学的开放获取数据库,供公众自由下载。不到24小时,论文被下载将近6万次,甚至一度导致网站崩溃。
霍金的这一席话,道出知识共享的真谛:
“我希望能激励世界各地的人们仰望星空,而不是只盯着他们的脚下。让他们想知道我们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并试着去理解宇宙。不仅是我的研究,而是每一个伟大的、具有探索精神的研究,对于任何人来说,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应该可以自由不受阻碍地访问。”
无论如何,疫情压力下的千呼万唤,终于换来了知网的改变。但是,在一种不够合理的产业格局里,这种来自消费者的呐喊,又能给垄断者带去多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最终又能持续多久呢?
霍金已经远去,当我们循着他的背影,试图眺望宇宙深处,眼前却横亘着知网们的庞大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