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利维坦公众号

利维坦按:和“白日梦”不同,“清醒梦”(又被称为“清明梦”)是在睡眠状态中做梦意识仍旧保持清醒,也就是说,“知道自己在做梦时做的梦”。你或许也有以下经历:在梦中忽然有一个具备意识的自我,以外在观察者的抽离视角来看待正在经历的梦境——你觉得自己已经醒过来了,但你其实还在梦中。如果这种梦是连环的(分层的),三层,四层,五层……要回到现实就更困难了。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宣称他在麻醉苏醒后,历经了100层的梦中梦,显示梦中梦的原理是脑部将肌肉无力误判成在床上醒来。
好吧,现实固然庸常,但可以想见,如果总经历“假清醒”,也无疑是件挺可怕的事情,这会让你的大脑认知产生混乱,所以个人并不建议“造梦训练”,当然,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多梦体质者,那又另当别论了。
文/Jake Rossen
译/杨睿
校对/石炜
原文/vanwinkles.com/lucid-dreamings-dark-side
本文基于创作共用协议(BY-NC),由杨睿在利维坦发布

图源:Van Winkle‘s
有人闯进你家里当然是种糟糕的体验。每天夜里,凯西都会听到门砰地一声响,看到枪口正对着他的脸,心脏跳得飞快。然后,他会从这个梦中醒来,安稳的现实带来的安慰蔓延到他的全身。再然后,他会再次醒来。
对于凯西来说,醒来并不是真正的醒来。这只是一个梦到自己醒来的梦,是在半意识的恐惧试图把他拖进更深层次的噩梦时挣扎到了意识表面。当他真正醒来的时候,他无法相信自己的感觉。他躺在床上扫视整个房间,寻找可以让他感受到现实的线索。在这个过程中,焦虑开始慢慢浮现在他的心头。
他说:“我醒来后发现有哪里不太对劲。就像我在梦里感受到的那样,像有什么东西正在侵蚀我。醒来很多次之后,最后一次醒来的时候,你还不能完全确定你是真的醒了。你确定这次的感觉不一样。但是其他那些假醒的时候,你也很确定感觉是不一样的。”
凯西是一名23岁的大学毕业生、餐馆经理。多年来,他一直有做清醒梦的经历。但他的经历与那些能轻松诱导、控制梦境的人截然相反。凯西并没有飞起来,他仍旧蜷缩在床上;他思考的也不是有关存在的问题,而是在思考自己清醒时的生活是否受到了影响。他说,生活的色彩仿佛消失了,某种让人毛骨悚然的威胁感在他周围流连忘返。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试着做清醒梦,希望能提高自己的感知能力、发掘新的创造潜力,或是找到欺骗身体的某种办法。对于一些人来说,深入到潜意识深层的实践非常有启发性。但对于其他人来说,我们也许真的不该用清醒梦去揭露那些常被隐藏在黑暗中的东西。
清醒梦简史
1911年,荷兰精神病学家弗雷德里克·范·伊登(Frederick van Eeden)首次使用“清醒梦”(lucid dreaming)这个术语形容个体在梦境中扮演积极角色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做梦者拥有自己的意识:他知道自己并不清醒,这让他有机会去参与那些对别人来说不可能的行为。
这很复杂,但结果据说很值得。人在清醒梦中得到的体验往往是迷幻的,通常会违背重力、自然规律,甚至是道德的约束。想和你的已婚同事一起睡觉吗?你可以。你们甚至还能骑到海豚身上去,甚至是想要去火星上也没什么问题。
你还可以解锁很多隐藏的秘密,找出复杂问题的答案。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披头士成员)的这段经历就很有名:他先是在清醒梦中听到了《昨日》(Yesterday)的复杂旋律,醒来后把它写了下来,传唱成了经典;科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也是在清醒梦中想出了原子结构的颠覆性模型。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清醒梦自然而然就来了。它们是零星、不可预知的;可能一辈子就一两次,或是永远都不会来。
但清醒梦的爱好者却能利用一些技巧去积极地引导清醒梦的产生。例如,一些人在醒来之后会立即写下他们记得的梦境细节,或是通过脑电波导引刺激思维,“深入探索”自己的夜间行为。这些技巧增加了做梦者对梦境中重复出现的元素的认识(如果一只粉红鸭经常在你梦里出现,你就会把它和一个梦联系在一起)。进入梦境之后,做梦者也会学着做“现实检查”,看自己有没有睡着。比如,拉一拉某根手指。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你就是醒着的。如果手指变长了,那你就是在梦里。这些预防措施,可以避免让做梦者混淆清醒和梦中的世界。
1975年,心理学家基斯·赫恩(Keith Hearne)的研究成果令清醒梦在学术界获得了颇高的声誉。赫恩表示,受试者能在睡眠期间与预先安排好的眼球活动进行交流,表现出某种控制感和感知力。

图源:ZME Science
事实上,对于这背后隐藏的科学,我们知道的还太少。清醒梦的做梦者正在经历一种混合式的快速眼球运动状态。他们并不是完全处于“正常”的梦境模式下。他们的大脑前额区域处于活跃状态,严格来讲,他们可以说是有意识的。
和任何影响现实的其他活动一样,清醒梦也有相应的亚文化群存在,他们会交流清醒梦诱导、实施及分析等方面的技巧。专家们几乎全都认为这是安全的。他们的推理是合理的:每个人都会做梦,所以清醒梦是安全的。
试想一下,如果你能操纵梦境,扩大对这个世界和你在这个世界中所处位置的理解,一切会变成怎样?
我们假设每个做梦的人一开始头脑都很健康。在某些情况下,你的卡戴珊式狂欢也许会因为碰到了一位亲戚,比如你的舅舅,就戛然而止,他把自己的一些幻想表现了出来。贾里德·齐泽尔(Jared Zeizel)是研究清醒梦的专家,也是《清醒梦操作指南》(The Field Guide to Lucid Dreaming)的作者。他提出:“清醒梦可以让你重新站到过去的创伤面前,那真的很可怕。”
心理学家蒂莫西·格林(J。 Timothy Green)等治疗专家已经成功用清醒梦治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21世纪版的催眠术疗法。在清醒梦疗法中,病人埋藏已久的记忆被重新带到意识表面,重新摆到病人面前,让病人去面对。但是如果没有专业的援助,面对这些恐惧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心理后果。
格林说:“人们完全有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些人想要接受治疗。但如果他们的生命依赖于此,他们就不想去接受治疗。”对于一个清醒梦者来说,这可能并不是他们可以选择的选项。“你打电话联系了数百名治疗师,里面可能只找到一个对清醒梦有所了解的人。”
做梦太多

图源:Van Winkle‘s
即使梦没有剥开做梦者的保护层,梦境中仍然可以出现一些会刺激做梦者的概念或想法。对于一些清醒梦者来说,这些经历可能就是他们的瓶颈,需要耗费更多的精神和情感去管理。
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做过清醒梦的亚伦·桑托斯(Aaron Santos)说:“白天,我会想前一天晚上梦到的事情。你知道做过一个紧张的梦是什么感觉吧,那种感觉一整天都会跟着你。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有点像是过着双重的生活。但你不能真的跟人谈起它。人们并不想听你昨晚做的5个梦,这些梦只能像秘密一样,被压抑在你体内。”

梦中梦就如同俄罗斯套娃,会经历诸多次“假清醒”。图源:Rusty Lake Blog
清醒梦会出现假醒的现象,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压力。对于经常梦到有人闯进他家的凯西来说,这种压力足以给他的清醒梦画上一个句号。噩梦还可以像套娃一样,一个又一个接连露出来。做梦者以为自己是清醒的,直到他们看到自己的双手融合在了一起或是注意到其他的信号,才知道自己仍然陷在一种混合式的意识当中,并没有真正回到现实。
自1975年开始做清醒梦以来,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oner)已经记录了1000多个清醒梦。他是《清醒梦:通向内在自我的门户》(Lucid Dreaming: Gateway to the Inner Self)一书的作者,还时常就清醒梦问题发表演讲。他认为,假醒可能是让做梦者最不安的经历。
“你觉得梦境已经准备好要崩溃了,你期盼着自己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看着自己记录梦的日记,但这些梦却是别人写的。于是你意识到你还在做梦。再次醒来,它又重新开始了。你从床上爬起来,看到浴室里的瓷砖居然是粉红色的。好了,你还在做梦。”
连续经历了7次假醒之后,瓦格纳有整整一年没有再做清醒梦。

《盗梦空间》剧照。图源:Giphy
那这种梦中的压力是否对我们的身体有害呢?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难以区分真实和想象。接下来这个实验就十分有趣:1996年芝加哥大学的一项研究让两组受试者练习篮球罚球;一组在真正的篮球场上练习,一组只在脑海里练习。之后,两组人罚球准确率几乎有同等程度的提升。这样来想,如果凯西多次梦到家被入侵,经历所有相关的恐怖,那不就是在重温过去的恐怖经历吗?
齐泽尔说:“我认为这可能是在重温生理反应。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我有压力的时候就会消化不良。当我在梦中感到有压力时,我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胃会有点疼。”
格林也认同这样的观点:“如果你在梦里有压力,它会让你心率加快、血压升高,产生你在清醒状态下受到压力会产生的所有生理反应。”
就其本质而言,清醒就意味着自我意识。这是一种警醒的状态,即便是睡觉也不会让人的感官变得迟钝。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清醒世界和梦境之间的模糊界限并不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后果。清醒梦可能对健康人是有益的。但对于那些饱受疾病困扰的人来说,清醒梦可能是毁灭性的。
在两个世界之间摇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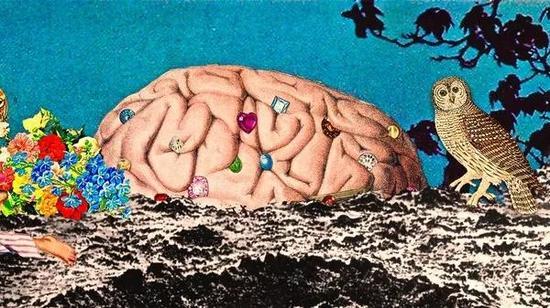
图源:Van Winkle‘s
2011年,贾里德·洛克纳(Jared Loughner)在图森市的西夫韦超市开枪,造成6人死亡,其他数人受伤,伤者中还包括当时的议员嘉贝丽·吉佛斯(Gabrielle Giffords)。没有人相信清醒梦才是让他这么做的罪魁祸首。发现了洛克纳的几本记梦日记后,媒体询问他是否因为沉迷于记录梦境,让他产生了一个分离性的清醒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不真实的。
曾经给洛克纳上过哲学课的老师肯特·斯林科(Kent Slinker)告诉媒体,他观察到这个学生的“精神被掏空”了,“他在往远处看,不是窗外,而是像有人在脑子里看一个场景一样。”
洛克纳自己的日记也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强迫式的做梦行为。当他不能做梦时,他甚至还会记录下自己的挫败感。2009年,他写道:“到目前为止,这个可怕的八月。。。。。。我很少做梦。。。。。。我很伤心。”
粗俗一点来讲,就是洛克纳的脑子出了问题。没有哪种研究梦境的科学能够改变这一点。但清醒梦可能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梦中的世界比现实生活中的这些俗事要更为可取。
虽然从生物化学的角度来看,清醒梦并不会让人上瘾,但一些清醒梦者却越来越频繁地去寻找他们梦境中无止境出现的画面;如果他们没有梦到更多这样的画面,他们就会感到不安,觉得烦恼。当然,任何让人身临其境的世界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2010年,有报告显示,观众在看完《阿凡达》后会出现抑郁,意识到现实世界并不那么有感觉。

图源:Van Winkle‘s
齐泽尔说:“这实际上还是回到了你最初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问题。你要考虑自己的目的。如果你的梦是关于幻想而不是自我发现,你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平凡的,而且你还患有抑郁症,那这一切都可以影响你。”
洛克纳的记梦日记被曝光之后,原先的猜测都纷纷让位,认为洛克纳的暴行是因为他挣扎在梦幻般的恍惚之中。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相。但难以区分真实世界和梦境并不完全属于法律上精神疾病的范畴。
“薇斯帕”(Vesper)是西雅图一位23岁的音频工程师,她有过一次清醒梦的经历。听说人们利用清醒梦逃避现实之后,她就开始练习做清醒梦了。几个月后,她觉得很难把梦中的记忆和真实的记忆区分开来。
她说:“我记得我去一家商店和那里的工作人员讲话,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个时候的我很内向,我经常会把梦和现实生活搞混,因为我的梦比现实更美好。我把它们记成了现实。”
有的时候,薇斯帕还会跑出去见见朋友,但她往往表现得不太理性。有意识的头脑告诉她,她是在梦中,可以过随心所欲的生活。当情况变得让她不舒服时她才会试着唤醒自己,结果却发现自己早就是清醒的了。
心理学家珍妮·加肯巴赫(Jayne Gackenbach)说:“我之所以对清醒梦心存担忧,是考虑到那些现实的边界比较薄弱的人。”她撰写了很多篇关于清醒梦的研究论文。“人们需要对自己的现实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孩子们可以做清醒梦,可以做得很好,但他们的现实仍然才开始没多久。这很相似。”
加肯巴赫以研究电子游戏在心理学上的逃避现象而闻名。在她的研究中,她看到了相似的现象:现实开始变得模糊的“转移效应”。
薇斯帕没有寻求专业的帮助。她只是不再尝试去做清醒梦。这样做之后,她之前的症状就都消失了。
在许多涉及人格解体的情况下,做梦者都会有某种现存的特征。清醒梦并不会凭空诱发疾病,但它有可能加剧它们。瓦格纳说:“我告诉人们,如果他们不能应付醒来后的生活,那就不要去做清醒梦。如果你不能专注于这个现实,那你就不能、也不应该去学怎么操纵一个替代的现实。”
不管做梦者健康与否,他们都是在和一个相对来说未经开发、了解甚少的领域打交道。人们想要利用自然学、遗传学等知识去抑制大脑的前额叶和顶叶;而清醒梦者则是想要点亮这些区域。
但我们到底是在增加感知,还是在剥夺它休息的权利?
加肯巴赫说:“把任何有创造力或幻想倾向的人推到一种新的情形,无论是毒品基地还是清醒梦或者假醒,那都是有风险的。人们以为这是一个安全的高度。但事实上,没有哪个高度是真正安全的。”
控制是一种错觉

图源:Van Winkle‘s
一些清醒梦者别无选择,他们本来没有进一步寻求启蒙的欲望,但自然而然就开始经历这些生动的梦境。其他人则走上了一条水到渠成的路,利用日记来回忆做过的梦,在睡前进行暗示,“训练”大脑欢迎清醒梦的到来。加兰他敏(galantamine)和褪黑素等药物也可以让人做梦,但一些医生并不赞成使用让睡眠类固醇含量增加的药物。齐泽尔说,一旦开始使用药物,人们很快就会放纵自己,形成依赖。
做梦者想要在晚上逃避现实,有时候可能反而会过犹不及。桑托斯每晚会做一两个梦,最多时可以做5个梦,这会一直不间断地刺激着他。
他说:“奇怪的是,我不记得我是比平常多睡了还是少睡了。但等我做一整夜的梦,醒来之后,我感觉到的并不是休息一夜后的放松和精力充沛。我觉得很疲惫,就像在办公室里度过了漫长的一天。肉体上的我体力充沛,但精神上的我却觉得被掏空了。”
当他担心疲劳会影响学习或人际关系时,桑托斯就会停止记录梦境。这些困扰也就平息了下来。他说:“几天后,我回到了正常的梦境。和清醒梦相比,我没有了千里眼。人想要做清醒梦是有身体和心理极限的,我想我已经达到了这些极限。”
瓦格纳也提到,对于大多数做梦者来说每个月4到8次清醒梦是最好的。他说:“你不能太过沉迷于做清醒梦。眼睛只盯着它的话,你会失去希望。”有一次,瓦格纳在梦中问自己的深层意识:身体健康的秘诀是什么?然后他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一切都恰到好处。”
经验丰富的清醒梦者要具备相对健全的头脑和身体,必须履行与适度饮酒者和周末比萨迷一样的责任:必须坚持适度的原则;必须注意过量的风险。即使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做梦者的控制也可能是一种错觉。
就像瓦格纳说的,“你可以影响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操纵它们,但你不能完全控制它们。你还要去应付波浪、水流和风。我是在比喻说,就像水手不能控制大海一样,做梦者也不能控制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