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费里尼:新新现实主义者,他用电影创造自我、梦境及一切
原创 深焦DeepFocus 深焦DeepFoc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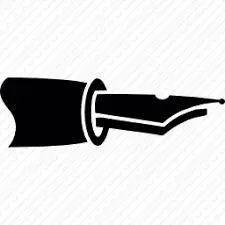
作者
Sight & Sound
February 2020
译者
武希钰
编辑
蘇打味
这位欢乐又独特的意大利导演从新现实主义传统中脱颖而出,创作了一系列奢侈且又随心所欲的电影,这些电影都像梦境般强烈。在英国电影协会(BFI)为庆祝费里尼诞辰一百周年而举办的大型回顾展期间,我们将探索费里尼作品中的某些主题,它们让这些作品成为20世纪艺术电影中无比绚烂的巅峰。
—— Pasquale Iannone
1920年代中期,意大利东海岸的里米尼镇上某个拥挤不堪的电影院里,一个小男孩坐在父亲的臂弯里,抬头盯着银幕上闪烁的影像。影院里闷热难耐,消毒喷雾刺鼻的气味久久弥散在座席周围,吸入喉咙就会黏附在气管,观众不由昏昏欲睡。男孩看得入了迷——他的心被银幕上的影像紧紧攫住:有色彩斑澜的异国女性,还有教堂、牧师组成的黑白影像。他正在看的电影名叫《地狱里的马其斯特》(Maciste all’inferno,1925),是这个传奇历险电影系列的最新一部,巴托罗密欧·帕迦诺(Bartolomeo Pagano)在其中饰演了与他同名的大力士角色。

时间切到四十年后:这个小男孩如今成了一位电影导演,名字叫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他在一部讲述自己生活和工作的纪录片《导演笔记》(A Director’s Notebook, 1969)中再现了这次发烧一样的首度观影经历。这绝不是费利尼第一次或最后一次深入挖掘他的童年经历——他在里米尼的首次观影中体验到的那种超乎寻常的气氛,将渗透进其后所有的电影作品中。
毫无疑问,费里尼是战后艺术电影的一位巨擘,其高度与同时代的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和黑泽明(Kurosawa Akira)相当。他的声誉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其时他的两部电影《大路》(La strada, 1954)和《卡比利亚之夜》(Nights of Cabiria, 1957)都在奥斯卡斩获奖项——这两部电影均由他的妻子、缪斯朱丽叶塔·马西纳(Giulietta Masina)主演。20世纪60年代初,《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 1960)与《八部半》(8 12, 1963)奠定了他的影坛地位,这两部电影的中心人物都是他那位备受欢迎的自我化身——马塞洛·马斯楚安尼(Marcello Mastroianni)。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费里尼的电影世界变得越发奢华、过度和梦幻。然而,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批评家都对他明显地退缩到自我放纵与唯我主义中感到失望。像卢齐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一样,他常因回避处理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现实而备受指责。

费里尼和黑泽明
对费里尼后期作品的这种简单化的议论一直持续到今天,特别是在英语世界中。诸如导演那种一向随心所欲的风格,对性别和性事的态度,以及对怪诞事物的拥抱,常常会惹人白眼。然而,在正视这些批评的前提下重新审视费里尼的电影作品,我们会看到一位在视觉上具有无比野心的艺术家,一位充分探索了电影自我表达潜能的导演。他始终如一执著探索电影本身的意义,也在漫画书与电影院、马戏团与电视机之间,探秘电影与其他文化形式的联系。
如果批判立场稍作改变,就不难发现费里尼在同辈电影制作者中的声誉一直很不错。甚至早在《大路》取得国际性的突破之前,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和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就曾挑选出他的作品加以称赞。在20世纪60、70年代,像肯·罗素(Ken Russell)、伍迪·艾伦(Woody Allen)、大卫·林奇(David Lynch)、亚历桑德罗·佐杜洛夫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这样的影人都曾向他找寻灵感(1990年费里尼拍摄电影《月吟》时,佐杜洛夫斯基曾到片场访问他,一见面,这位智利导演就伸出双臂,兴高采烈地向他打招呼:“爸爸!”)。而在意大利当代电影制作者中,保罗·索伦蒂诺(Paolo Sorrentino)无疑是最明显地沿用了费利尼模式进行创作的一位,尤其在诸如《家庭朋友》(The Family Friend, 2006)和《绝美之城》(The Great Beauty, 2013)这样的作品中,他那无比欢乐的巴洛克套路以及对怪诞的喜爱展露无遗。索伦蒂诺确凿证实了(也正如最近越来越多的评论者和学者所论证的那样),不论费里尼关注的对象是软弱的小镇青年,还是大城市里的风云人物,他都远非一个不关心社会政治的寓言家:他不仅是20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最重要的编年史家之一,更是意大利最伟大的电影人之一。

为纪念费里尼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将在伦敦的英国电影协会南岸进行为期两个月费里尼电影回顾展的展映,重新发行《甜蜜的生活》,并计划在英国各地进行展映。在此,我们探讨了一些关键主题,正是这些主题使得费里尼的电影生涯成为所有影人中最为独特的一个。
本次费里尼回顾展在伦敦的英国电影协会南岸举行,将一直持续到二月底。此次回顾展是致敬费里尼系列的第一步,由意大利文化部组织协办,即将去往世界各地的电影协会。《甜蜜的生活》的4K修复版本现已在英国的电影院上映。
费里尼:新新现实主义者
Fellini: The Neo-Neorealist
by Philip Kemp

费里尼作为一名电影导演,他的根基深深扎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土壤中。他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做编剧,由此涉足电影界,曾参与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Rome, Open City, 1945)、《战火》(Paisà, 1946)等电影的剧本撰写,也曾与新现实主义影人如皮亚托·杰米(Pietro Germi)和阿伯特·拉图尔达(Alberto Lattuada)合作。他初涉导演就是和拉图尔达合作的,二人共同执导了《卖艺春秋》(Lights of Variety, 1950)。
费里尼独立导演的前五部电影——《白酋长》(The White Sheik, 1952)、《浪荡儿》(Ivitelloni, 1953)、《大路》(La strada, 1953)、《骗子》(Il bidone, 1955)、《卡比利亚之夜》(Nights of Cabiria, 1957)——都借鉴了新现实主义传统,不过自《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 1960)以降那些日渐丰富了他作品的幻想元素,早在初期就已经开始渗入些许特质。值得一提的是,费里尼尚未去到罗马,还在家乡里米尼时,起初曾是一位漫画家,即将为《飞侠哥顿》连环画写作意大利语对白。由阿尔伯托·索尔迪(Alberto Sordi)饰演的《白酋长》的男主角是当时广受欢迎的fumetti(一种仍在用真人相片而非绘制图画的连环漫画)中的明星。

《白酋长》(The White Sheik,1952)
尽管如此,费里尼在早期电影中描绘意大利时,还是一再采用新现实主义者所青睐的那种忧郁视角:这片土地不同于游客照片里那样,充斥着浪漫的教堂与古老的废墟、熙熙攘攘的街道和一盘盘堆得高高的意大利面。费里尼这些电影呈现出的意大利通常惊人地真实。海风拂过沙滩,宛如狂风卷过后垃圾四散的夜间广场般荒凉,让人不由想起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的画作,想起小镇郊野地带绵延数里的平坦丛草地。在《卡比利亚之夜》(由费里尼的妻子朱丽叶塔·马西纳主演)中,女主人公极其珍视的房子不过是一个煤渣水泥砖砌成、又丑又小的方盒子,坐落在一片灰秃秃的荒原上。《白酋长》开场的镜头中也出现了类似这样偷工减料的建筑物。

《卡比利亚之夜》
费里尼的早期电影和新现实主义者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那些前理性或非理性的角色——孩子、小丑,乃至像《大路》中的杰索米娜(Gelsomina,又一次由马西纳饰演)那样的傻瓜——在影片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浪荡儿》的最后一幕中,由弗朗科·英特朗吉(Franco Interlenghi)饰演的摩拉德(Moraldo)摒弃了里米尼幼稚的乡绅风气,只身前往罗马,像极了费里尼自己15年前所做的那样。但影片最后的镜头落在那位与摩拉德在车站聊天的年轻小伙子身上。我们在《八部半》(1963)中看到的最后一个人,是饰演年轻时的圭多·安塞尔米(Guido Anselmi)的男孩(马塞洛·马斯楚安尼在片中饰演另一个费里尼的人物),他携着长笛和白色披肩,带领我们进入黑暗环绕之处;而在《甜蜜的生活》的最后一场戏中,长着一张甜美脸蛋的翁布里亚姑娘保拉(Paola)试着想对男主角马塞洛(也就是马斯楚安尼)说些什么,沙滩上的他在滔滔巨浪中却听不到她的声音。杰索米娜生性天真、率性,心境常常在快乐和悲伤之间转圜,本质上是个孩子,而那个倒霉的罗马妓女卡比利亚也不比她聪明多少。她反复遭受欺骗、虐待、背叛,直至陷入绝望的深渊(“杀了我吧!我不想活了!”),然而不一会儿,当她看见一群街头艺人走过,就又能绽开笑颜。

《八部半》(1963)
归根结底,所有这些非理性的人物或许都是费里尼自己的化身——或是他一直想成为的人。“我并不认为运用理性是接受所有艺术作品必不可少的步骤,”他曾这样说过,并特别谈到《八部半》,“如果你被它打动了,就不需要别人为你解释。”
费里尼风格
The Felliniesque
by Pasquale Iannone
费里尼是为数不多几个风格极为独特的导演之一,以至于衍生出一个形容词。就像我们常说的“林奇感”(Lynchian)一样,“费里尼式的”(Felliniesque)往往被用来指称任何模糊而奇幻、梦一般的神秘,甚至纯粹非现实主义的事物。虽然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费里尼的方式早先铸就于战后新现实主义“走到大街上”的时代,其时,他曾与导演罗伯托·罗西里尼合作,写作包括经典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1945)和《战火》(1946)在内许多影片的剧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当他们想象何为“费里尼式的”时,脑海里常常会浮现出一种风格,这种风格是在电影制片厂的“玩具盒子”里创造出来的,也依赖于“玩具盒子”——特别是罗马的奇尼奇塔电影城(Cinecittà)。

费里尼(右)和罗西里尼(中)
1968年10月,《综艺》(Variety)杂志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罗马的奇尼奇塔电影城随着费里尼《爱情神话》(Satyricon)的开拍变得热闹非凡”。时任这所世界知名的电影制片厂负责人的帕斯奎尔·兰西亚(Pasquale Lancia)证实,费里尼的这部罗马史诗很快就将在他的摄影棚里拍摄足足6个月,“奇尼奇塔电影城的大部分人手都忙得不可开交”。
很少有电影制作者像费里尼这样清楚如何让奇尼奇塔电影城为他忙碌。尽管他的早期电影在制片厂作业以外,也融合了一些外景拍摄,但是这位导演日渐对一个想法萌生了兴趣:从零开始建立他的电影世界,并对其施加完全的控制。1986年,费里尼接受《正片》(Positif)的吉恩·吉利(Jean Gili)的采访时,重申了自己的信念,即摄影棚是唯一一个能让导演确切地重现他或她在想象中虚构的事物的地方。费里尼告诉吉利,就像画家在画布上作画一样,导演“能够把色彩和色调组合在一起,调控距离、透明度和视角”。20世纪30年代末,电影制片厂刚刚开张不久,费里尼就以一名年轻记者的身份首次踏入了奇尼奇塔电影城。正如他生命中的许多其他重要时刻一样,费里尼在1987年的《访谈录》(Intervista)里把它搬上了大银幕,这部电影本来就是为了纪念电影制片厂开办50周年而构思的。

费里尼总是把他的电影想象成一段旅程,很明显,不论在摄影棚内外、是否以几个主角为中心,他的大多数作品都具有一种不安分、飘忽不定的气质——导演声称这是他和罗西里尼合作带来的影响。费里尼的电影常常充满了动感,他的人物在拥挤的画面中进进出出,一些人物甚至自由地打破了第四堵墙——像《卡比利亚之夜》(1957)著名的结尾镜头,也体现在《阿玛柯德》(Amarcord,1972)以及别的作品中。
旋转的视觉效果与同样自由漂浮、且由后期合成的的整体声景相匹配,这些声景将对话、音效和音乐分层。费里尼对待声音和对待图像一样,热衷于监督每一个细节。如果他觉得一个演员的声音与他的相貌不匹配,或者他希望演员的声音能和外貌形成鲜明对比(比如说为了喜剧效果),他就会改变它。所有曾经和他一起工作的演员都清楚,他们在片场所说的台词往往在后期制作中会被加以修改。在费里尼漫长的职业生涯中,配音在大多数意大利影片中都是一种常态,但对费里尼来说,配音独具某种诗意。正如法国作曲家、电影理论家米歇尔·希翁(Michel Chion)指出的那样:“我们已经抵达这样一个阶段,声音 […] 开始在某种巴洛克式、去中心化的繁盛中获得某种自主权。”

《阿玛柯德》( Amarcord,1972)
或许,对于费里尼果断转向以摄影棚为主的电影摄制这件事,最简白的解释出自吉利的采访。采访中费里尼被问到,为拍摄1983年的《船续前行》(And the Ship Sails On)而建造一片完全由塑料制成的海是否让他感到可笑,费里尼答道:“如果你想赋予大海某种感觉——让这片海具有某种特殊质地——你就只能使用易于以某种方式被照亮的材料来达到这种效果,如果你这样做了,它们就会变得 […] 富于感情。”
费里尼影像里的费德里科
Federico by Fellini
by Julia Wagner
费里尼的电影和费里尼其人有时似乎存在于同一个奇幻世界里,这位导演如此充分地将自己的经历、记忆和梦所启发的自传线索编织到他的作品中。
早在《浪荡儿》(1953)中,费里尼就开始从自己的生活中找寻灵感。这部电影描绘了一群年轻人在亚得里亚海岸边的一个滨海小镇上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与导演的早年生活形成了对照。主角摩拉德是费里尼的化身,他对里米尼小镇的生活方式感到窒息,于是——就像导演自己所做的那样——最终他乘一趟火车离开里米尼,前往罗马。费里尼将他的兄弟里卡尔多(Riccardo)选作帮派成员之一,突显了影片的自传性共鸣。

《浪荡儿》(1953)
银幕上出现导演的自我化身是费里尼电影一个常见的特征,其中最有名气的是演员马塞洛·马斯楚安尼,他那英俊、性感、魅力四射的明星形象可能是导演个人美好愿望的投射。费里尼的六部电影都有马斯楚安尼参演,最早一部是轰动一时的《甜蜜的生活》(1960),这部影片反映了费里尼所生活的罗马在当代艺术和演艺业方面的环境;最后一部是费里尼1987年拍摄的《访谈录》。这六部影片中最重要的一部是《八部半》(1963),马斯楚安尼在其中扮演圭多,一个创作灵感陷入停滞的导演。马斯楚安尼在影片中的形象经过调整,与费里尼愈发相似:他的头发灰白,鬓角和胸毛都剃光了;他被鼓励模仿费里尼的步态,戴着同样风格的帽子。《八部半》含有好几种自反性的手段,包括对圭多电影的批评,也经由制片人和评论家之口,通过说出费里尼所期待的评论而被纳入其中;不仅如此,影片片名也反映了费里尼到那时为止所拍摄的电影数量。

Federico Fellini, Marcello Mastroianni
这种自传性也通过涉及费里尼的梦从而进入到他的电影中——这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第一次阅读卡尔·荣格(Carl Jung),并开始在笔记本上记录自己梦境细节后,就越来越感兴趣的领域(最终他于2008年出版《费德里科·费里尼:梦书》(Federico Fellini: The Book of dreams)一书)。
特别是导演的第一部彩色电影《朱丽叶与魔鬼》(Juliet of the Spirits, 1965)的灵感就来自于他对精神领域与荣格精神分析法的迷恋。这部电影是用极其炫目的迷幻色调拍摄的,由他的妻子朱丽叶塔·马西纳饰演一位性压抑的家庭主妇,通过幻想和通灵聚会探索自己的欲望和恐惧之后,获得了独立。鉴于费里尼自认的花花公子与通奸者的身份,像这样的演员阵容和情节令我们不由地会思考,朱丽叶/朱丽叶塔在此处作为一个丈夫风流成性而遭遇冷落的妻子,究竟有何意义。

费里尼在他的电影中也常常提到他自己生活中独具意义的地方。例如,《罗马风情画》(Roma, 1972)讲述的是导演抵达罗马城的情形,与古罗马的幻景交织在一起进行呈现,而《阿玛柯德》(1972)则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在里米尼周边法西斯的统摄下,一些角色长大成人的故事,正如费里尼本人的经历一样。在当地的习语中,影片片名“阿玛柯德”的意思是“我记得”——但这个“我”是谁,究竟是谁“记得”,主人公,还是导演本人?费里尼对主体性的戏谑态度也在纪录片风格的讽刺电影《导演笔记》(1969)和《访谈录》中有了更清晰的体现,在这两部影片中,他扮演了一个角色:“费德里科·费里尼”。
费里尼作为自传性导演的名声或许会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但他经常在采访中否认他的电影是根据自己的生活改编的,而更倾向于强调想象力在他的创作中的作用。正如他在1980年说过的那样:“我的电影不是由记忆主导的。说我的电影具有自传性是一种过于肤浅的清算,一种草率的分类。在我看来,我几乎创造出了所有东西:童年、性格、乡愁、梦境、记忆,只是为了能够愉快地讲述它们。在故事层面,我的电影里没有什么是自传性的。”

当然,费里尼作品中的设计、拍摄风格、表演和化妆都让人们注意到他电影世界的建构性:这是一个想象中的地方,而不是现实。费里尼并不在真实的外景中拍摄,而是尽可能创设场景,让那些自传性元素激发的事件浸润在幻想中,还会给演员的台词配音,从而让影片更加接近他的想象。与此类似,在他作品中反复出现马戏团和游街的譬喻提示我们,对费里尼来说,电影是一种奇观,是为了讲述和观看的乐趣而上演的,是一个表达内在精神而不是展现历史真相的空间。
最终,“费德里科·费里尼”成了导演最经久不衰的角色——一个不可靠叙述者,一个依托大银幕与公共生活构建起来的自传性主题。“费里尼”在多部电影中出现,累积而成一个独特的形象,结合了inetto(无能的男人,正如杰奎琳·赖奇在2004年出版的《超越拉丁情人:马塞洛·马斯楚安尼、男性气质与意大利电影》一书中描述的那样)、极具创造性的天才(马戏团的头目)与受困于对女人的欲望的男人。
费里尼电影家族
La Famiglia Fellini
by Philip Kemp
在费里尼的职业生涯中,他的身边经常聚集着一群亲密无间的合作者,几乎组成了一个家庭(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确实是相互联系的)。其中最有名的是作曲家尼诺·罗塔,从《白酋长》(1952)到《管弦乐队的彩排》(Orchestra Rehearsal, 1978),他为费里尼所有独立执导的作品配乐——如果他没有在1979年去世,他毫无疑问也会为费里尼剩下的几部作品配乐。费里尼曾回忆说:“我合作过的同僚里最珍贵的是尼诺·罗塔——我们之间,总是很快就能达到完全的和谐。”

费里尼和尼诺·罗塔
还有一些人对费里尼的忠实程度也与尼诺·罗塔差不多。恩尼奥·弗拉亚诺(Ennio Flaiano)、图里奥·皮内利(Tullio Pinelli)曾与费里尼共同编写过几部电影的剧本;早年时奥泰洛·马尔泰利(Otello Martelli)常常担任费里尼的摄影师,后来朱塞佩·罗通诺(Giuseppe Rotunno)接任了这一工作。演员马斯楚安尼的兄弟鲁杰罗·马斯楚安尼(Ruggero Mastroianni)担任费里尼电影的剪辑师足有二十多年。艺术指导兼服装设计师达尼洛·多纳蒂(Danilo Donati)将他极具特色的造型运用到费里尼许多视觉效果更为奢华的电影中,如《爱情神话》(1969)、《罗马风情画》(1972)和《卡萨诺瓦》(Fellini’s Casanova, 1976)。布景设计师丹提·费瑞提(Dante Ferretti)最初是费里尼的门徒,后来又参与到他的五部电影当中。从《爱情神话》开始,导演就经常倚仗诺玛·贾切罗(Norma Giacchero)监督剧本,以保证剧本的连贯性——据大家说,这份工作需要相当的机敏。

Federico Fellini, Marcello Mastroianni
当然,还有演员——尤其是马塞洛·马斯楚安尼和朱丽叶塔·马西纳。从《甜蜜的生活》(1960)开始,马斯楚安尼多次扮演费里尼的化身——最明显的一次就是在《八部半》(1963)中,他扮演的角色圭多·安塞尔米是一位著名的导演,却无法为自己的下一部电影想出一个点子。即便在《甜蜜的生活》和《女人城》(City of Women, 1980)中,他也演绎了导演费里尼的一些面向。在这两部影片里,他饰演的角色名字还叫圭多。费里尼与马西纳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他们在1942年相识,当时她在广受欢迎的系列广播喜剧《奇科和帕里娜》(Cico e Pallina)中扮演帕里娜(Pallina)一角,而费里尼正在为这部剧撰写剧本。一年后他们结婚了,她在他的电影中演出的次数比其他任何演员都多:总共七部。出人意料的是,直到马西纳参演的倒数第二部电影《舞国》(Ginger and Fred,1985)里,她和马斯楚安尼才同时被费里尼选中,得以首次合作。在这部影片中,他们二人饰演了一对元老级的舞蹈搭档,三十年后得以重聚。(这部电影的制片人被金格尔·罗杰斯(Ginger Rogers)告上了法庭,显然深受后者回避幽默、不解风情之苦。)

Federico Fellini, Marcello Mastroianni and Sophia Loren
其他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不那么亲近的合作——也为费里尼的作品提供了养分。当然包括他最初合作过的新现实主义导演,还有自己的童年经历:木偶剧、马戏,以及像《孩子们的信差》(The Corriere dei piccoli)这样的连环漫画杂志,上面刊载过美国漫画家温瑟·麦凯(Winsor McCay)和乔治·麦克马纳斯(George McManus)的作品。所有这些都为他的电影增添了更多奇幻色彩。
考虑费里尼作品受到过哪些关键影响时,我们很难忽略天主教会——即便它对费里尼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八部半》中,对圭多·安塞尔米童年时期的闪回唤起了费里尼幼时在牧师的抚育下成长,忍受过的那种严酷而压抑的经历,不仅如此,费里尼常常在对宗教人物与事件的描绘中获得某种报复的快感。《甜蜜的生活》里,男主角、记者马塞洛和他的同事们争先恐后地围住那三个声称在田野里看见圣母玛利亚的孩子;《骗子》(1955)里的三个骗子扮作神父,哄骗容易轻信的农民;1957年的影片《卡比利亚之夜》中(电影里的这个序列最初在教会的坚持下被删掉了,直到最近才得以修复),卡比利亚参加了一个宗教的庆祝活动,这一活动被费里尼嘲弄地表现为一场何其虔诚的狂欢。如果说马戏有时像是费里尼的宗教,那么宗教则常常被费里尼不无讽刺地表现为一场闹剧。
原标题:《四度狂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他用电影创造自我、梦境及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