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当我们谈论王者荣耀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5月15日晚,我们邀请了周逵、黄典林、董晨宇三位青年传播学者,通过线上对谈的形式,分享了他们眼中的游戏研究。本期推送为你整理了三位老师的核心观点。
全文共9319字,阅读需要大约23分钟。

董晨宇:我们这次对谈的题目叫做“当我们谈论王者荣耀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当然,这个题目只是一个引子,一是因为我们如今一想到游戏,就会想到王者荣耀,二是因为我们三个人也都是这个游戏的玩家。
我们今天的对谈,会从王者荣耀出发,和大家来聊聊游戏这件事。为了让我们的讨论更有逻辑,我们先来建立一个问题框架。简单来说,我们会聊四件事:
(1)游戏为什么值得研究?
(2)如何进行游戏研究?
(3)如何理解玩家?
(4)对于那些感兴趣游戏研究的人,我们可以给出什么建议?
01. 游戏为什么值得研究?

董晨宇:对于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来说,它必须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也就是说,我们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游戏需要传播学,或者反过来,为什么传播学需要游戏?
黄典林:我是做文化研究的,文化这个概念囊括了一切东西,包括这里讲的游戏。游戏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东西,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游戏和整个文明是同步的。所以,我们要回到这样一个宏大的视野,看待游戏的意义。
我想起了一个人,荷兰的文化史学家、语言学家,也是游戏学的创始人,叫约翰·赫伊津哈,他写过一本《游戏的人》。他认为人除了理性的一面(经济学)、政治的一面(政治学),还有玩乐的一面。在游戏中,人纯粹是基于一套规则来满足自身的快乐需求。现在有一个词,叫做Ludology(游戏学),就从这个地方演变过来的。从这一点来讲,游戏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它本来就是人类文明、日常生活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不是说你贬低它,你觉得它没有意义,或者说你忽略它,它就不存在了。
第二,回到我们的专业。我们都是做媒介研究的。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多媒体形态下的游戏,算不算一种媒介呢?这对我们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我们所理解的媒介是什么?还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大众传播吗?游戏有没有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媒介的新的界定?游戏研究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去重新反省我们对媒介技术的各种理解方式。我认为,这些方式如今需要重新推倒出来,或者说至少去修正,更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

周逵:游戏研究在中国被逐渐认可,也是一个过程。早期会有学者认为游戏研究不是传播研究的一部分,因此有一些这方面的论文也会遭受拒绝。2017年,刘海龙老师在《国际新闻界》组了一个游戏研究的专题,我最近听说,还有一个刊物也在做这件事情。从这个经验抽象出来看,我们所遭遇的其实是一个游戏的正当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关于整个娱乐观念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如何去理解娱乐的正当性。
从西方的维度来看的话,娱乐的正当性是从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被确立之后、社会结构经历转型之后,才有的这一套东西。在中国,可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逐渐接纳了娱乐(改革开放之前叫文艺)。中国第一个以“综艺”命名的节目是1990年才出现,到今年正好是30年,就是正大综艺和综艺大观,所以,这其实都是我们整个观念史的一部分:我们如何接纳一个可能并没有直接社会生产意义,甚至是没有革命意义的东西?要知道,当年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其实是把整个文艺都嵌入到一个巨大的革命机器里面的,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功能性,到1979年以后我们开始慢慢变化。
可能在座很多的人在个人经验里都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玩游戏机被家长“撵”过。当时的游戏机厅都是在一些就是听上去很“社会”的地方,它是一种非法的灰色经济地带,但是现在来看,世界最知名的电子竞技比赛是在鸟巢举办的、是登堂入室的,还进入到亚运会的表演赛里。所以,它在主流的象征性符号秩序中,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正当性,这背后折射了我们整个娱乐观念的变化。当然,其中有产业力量的助推。
但反过来讲,游戏产业还在不断被要求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所以你看到,现在的游戏公司在价值观设定,内容设计等方面,也在试图把自己变成一个具有一定社会功能的东西。王者荣耀就在强调这一点。这款游戏的皮肤里包含了敦煌的飞天、昆曲等等元素,它也在试图镶嵌进入我们之前的合法性体系内,用既有的一些符号来证明它的正当性。

董晨宇:我在想的角度有一些不一样:我下午还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传统的“主流”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否也曾存在“游戏”的影子呢?我想到了那本著名的《独自打保龄》。保龄球其实就是一种游戏,虽然在这本书中,保龄球更多具有比喻的意味。这么看来,虽然我们对于游戏的研究热潮,可能仅仅是十几年的历史,但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于游戏本身,其实关注一直是非常多的。
作为传播学者,我会想的第一个问题是:游戏如何镶嵌进学术研究的脉络中?我个人认为,在研究游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游戏+”。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定要在“游戏”后面,加一个看起来更具有本质性的东西。我们知道,游戏研究的学术期刊中有两本比较重要:Game Studies和Games and Culture。我们阅读这两本期刊的时候,会有一些不适感,因为文章之间的“可对话性”是非常差的。这和传播学曾经经历的东西很相似。借用施拉姆的话来说,游戏研究也是一个十字路口,可能还要更糟糕一点,它可能是西直门立交桥。正因为每个学科的人都会去进入,所以“游戏+”就特别重要。对于传播学者而言,游戏研究的意义,就是将游戏和传播并置在一起,我们可以衍生出很多的思考,例如有一篇学术随笔,题目叫Why Game Studies Now,作者y提了很多典型的传播问题:
-- 用虚拟、游戏调节的社会关系取代现实世界关系,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
-- 不同的游戏、代码和交流形态,会不会产生不同的后果?
-- 对现实生活中极度缺少公共交流的人来讲,游戏可否提供一些新的机遇?
-- 游戏如何放大和改变既有的社会关系?
-- 如果一家人不看电视了,开始一起打游戏,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 如果朋友们不一起喝一杯了,而是晚上在英雄联盟里共度四个小时,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 当游戏变成移动的、无线的、网络的之后,一切又会发生什么改变?
02.我会如何进行游戏研究?

董晨宇:既然我们说游戏研究有价值,那么,我们需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便是,我要如何进入游戏研究?每个人的视角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三个是否可以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提供一些个性化的视角?
周逵:最早我写过一篇论文,发在《现代传播》上,叫做《作为传播的游戏——游戏研究的历史源流、理论路径与核心议题》,把游戏的研究的脉络大概梳理了一下。到2017年的时候做了一个蝙蝠侠VR的研究,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现在我自己的兴趣主要是对游戏文本的分析。比如从王者荣耀的角度来讲,它里面有很多英雄,这些英雄他是怎么被塑造出来的?其实我们每个文化里面都有一个英雄塑造的问题,例如我们在1949年以后的革命时期中,是怎么塑造英雄的?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影视剧里又是怎样塑造英雄的?再到如今的这种“电子神话学”中,英雄又是如何被塑造的?我觉得西方的英雄塑造大概有四个阶段:
1
第一个阶段叫神话英雄类的,比如说奥德赛。他是以神力造福于人的,就是开挂的一个神仙。当然,这个神可能是有缺点的
2
第二阶段是西部英雄时代,它象征的是前工业时代、牛仔式的、个人主义的一人一马。比如说《荒野大镖客:救赎》,就是西部英雄时代的故事,这种一人一马个人主义的东西,在王者荣耀里,我觉得跟刺客比较像。
3
第三个阶段是超级英雄时代,就是我们说的漫威,它大概是和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情境有关系,你看到大量的都是科技和后人类的隐喻。漫威英雄中的钢铁侠就是一个标准的后工业时代的英雄塑造方法。所谓“穷人靠变异,富人靠装备”,钢铁侠就完全是富人这套方法,靠装备变成一个超级英雄。
4
第四个阶段,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单个出道的英雄不行了。在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气氛是渴望“集体出道”的英雄,也就是建筑在个人主义之上的集体主义。因此,2008年以后,有大量的这种成团出道的英雄,包括漫威和DC。
我觉得王者荣耀特别棒的地方在于,它同时包含了这四个阶段:它有后羿、盘古,这些就属于叫神力造福于人的英雄;也有一人一马式的,比如说此刻;也有超级英雄式的,比如说鲁班;也有成团出道的,比如说长城护卫军。它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在对标中国的电子神话时代,以前我们好像挺缺这套东西。

黄典林:周逵刚才说了很好的思路,更多的是从文本的角度去讲。我一直在思考问题是:这些新的技术形态出现以后,原有的思维方式将会发生什么变化?相应的,理论应该发生什么变化?比如说VR游戏,这种更强调全身心沉浸式介入的游戏,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要去思考,因为这是个统领性的问题。
首先,在传统理论里面,我们会强调技术和社会的关系。过去我们特别强调,技术是由社会决定的,但今天还是不是这样?当人工智能、算法这些东西出现以后,社会决定的程度是不是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这是游戏给我带来的第一个思考,因为游戏内部的语法关系是高度复杂的,玩家在玩游戏的时候,所生成的复杂性、多样性,超出了技术设计的范畴。这是第一个问题。
除了对技术的理解,游戏研究也能够提醒我们对传播研究的其他概念进行反省和修正,比如,传统视角中文本是相对静态的,但游戏的文本更多是一种text-in-use,就是它不是一个你可以在研究之前就可以直接面对的既有的东西,而是一个具有极强的互动性和实践性的有待生成的东西,必须在使用或者行动中才能够去观察到它。

再比如,我们怎么理解玩家?过去的观众在看电视时,TA是积极的、阐释的。可是今天,“积极的受众”这个概念已经不能解释玩家在干什么,因为他不只是在阐释,同时还在创造和互动,他不仅跟游戏本身互动,同时还跟其他玩家、跟各种各样的社会元素互动,这个互动性要比任何其他媒介形式强很多。
除此之外,玩家不只是在规则设定的互动模式中对游戏人物和叙事结构进行阐释,同时还在体验。体验不仅是一种意义阐释,还有身体感受。这些东西在过去的媒介里可能都没有,或者不那么凸显,因此就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身体的全面介入。比如VR游戏里,整个身体和感官系统都要充分调动起来,玩家由此获得的身体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周逵:我在这里插一句,即便没有VR时,当年我们最早玩的那个实况足球,你也经常看到一个人拿着手柄,手上摁射门,然后脚上也跟着踢。

黄典林:是的。同样是在使用一种技术,但使用的方式却发生了变化:从阐释到体验。除此之外,游戏文本和传统媒介文本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我们看一个电视剧,它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文本,结构是很清晰的;但游戏不是这样,游戏的互动性太强了,它总是在不断的变化。它既有结构,但更多的是不确定性和生成性。最后,传统的媒介技术无论是组织形态还是空间结构上都是相对比较集中的(比如在家里看由专业媒体提供的电视节目),但是今天的游戏玩家不是。我们看到,移动互联网加上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已经使得“万物皆媒”。我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场景中,都可以迅速切入到游戏环境内部。
董晨宇:我来分享两个比较微观的话题吧。第一个话题是“化身”。化身与自我之间是有关系的,比如一个喜欢玩蔡文姬的人,在领导力这个属性里相对差一点,因为她是一个纯辅助,自己没有任何伤害。那么,游戏世界中的化身,有没有可能就像Belk所讲的,是一种自我的延伸(self-extension)呢?Belk曾认为,物是一种自我的延伸。例如犯人在进监狱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剃头,不管你是梳着什么样的头,都要剃成平寸;不管是带着什么佛珠、手串,全部都要收回去;不管你穿什么衣服,全部都换成狱服。通过剥夺你这些物,其实剥夺了你的某一部分自我。2013年的时候,Belk提出数字空间中的非实体的物,其实也是一种数字自我延伸(digital self-extension)。
第二个话题,是我自己蛮感兴趣的驯化研究。“驯化”最早是来自北欧的研究界,他们会关注一个家庭如何去驯化新买的电视,如何把电视从一只野猫变成一只家猫。这些早期研究已经有很大的问题了,比如说,他们关注的电视,是你不能抱着上下班的,于是他的分析是在“家”的范围之内,分析单元也往往是一个家庭。然而,随着个人移动媒体的出现和普及(比如王者荣耀),我们的分析就要做出改变。
驯化研究可以是非常微观的。我特别喜欢一种人类学的视角,就是说这世界上其实没有王者荣耀——中学生玩王者荣耀,和上了班的人玩王者荣耀,他们眼中和使用的王者荣耀不是一个王者荣耀。这是我们理解游戏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

比如我看到一篇2014年发表的论文,研究老年人如何驯化电子游戏?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很少人会关注,老年人为什么打游戏?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这件事有点意外。这篇论文给我的启发就是,老年人购买和使用电子游戏的动机,以及老年人对于游戏意义的建构,不但是年轻人想不到的,就连游戏的设计者都想不到。我可以举其中几个理由:
(1)了解新技术,不要被时代抛弃;
(2)在游戏中实现自己年轻时未尽的梦想;
(3)通过游戏,与晚辈拥有更多共同语言
(4)利用解谜类游戏进行认知训练——即便很多游戏被开发的初衷并非如此。
周逵:我还想回到文本的角度,其实我们从游戏的文本里头可以做很多分析。比如王者荣耀里就有一种类型的英雄——魔种。魔种有两种:一个耳朵是红的,另一种是会变异的。比如张飞、孙悟空、百里玄策都是魔种。在整个西方的科幻文学里,有一个词叫mutant,就是异种、异类或异变体就可以对应魔种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可以做交叉研究的,比如从叙事上讲,有没有魔种主义?
刚才说到王者荣耀中的五虎上将,那么,我们还可以思考,三国文本是怎么引进来的?还有我们提到了长城守卫军,我特别喜欢这个板块,因为长城守卫军里是各种各样的人,有魔种、有异域的人,还有被流放的人,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主体,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当然,你还可以从女性主义来分析王者荣耀中的女性形象。这在文化研究和游戏研究中也很多。最早很多人批评超级玛丽,质疑为什么是玛丽(男性)去拯救一个公主(女性)。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游戏,叫古墓丽影,大家的评价普遍比较高,因为它塑造了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角色,所以特别受到女性玩家的欢迎。反过来你也可以观察王者荣耀,它如何结合古典和现代对于女性的审美,王者荣耀中有很多女性形象是非常“飒”的,比如钟无艳。
03.如何理解玩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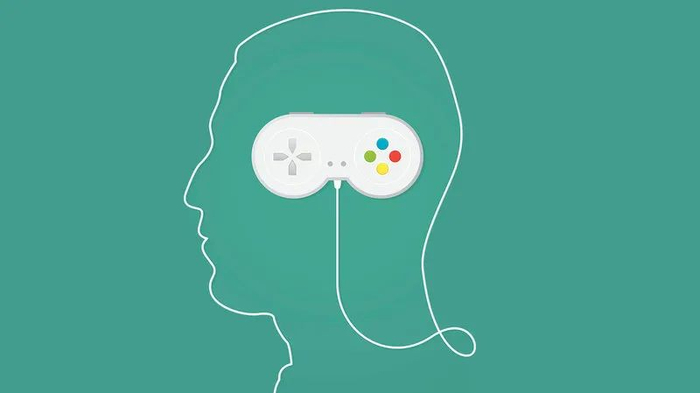
黄典林:玩家实际上可能是游戏研究中非常具有创新的一个点。虽然说我们过去也研究积极的受众、多意的阐释,但用这些东西来研究玩家,可能不太合适。比如,在研究界出现了所谓的“游戏学转向”,因为它更多强调游戏的实践性,你需要去“玩”,才能够进入到这个过程当中,才能体会到它具体是如何展开的。单纯说玩家是积极的,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对于玩家群体,也许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思考:
第一个是玩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玩,TA所处的文化、制度、技术/物质条件是什么。玩家不可能在一个真空中玩游戏,我们玩的游戏是被设计好的,具有一定的物质性。在游戏研究中有一个词,叫做配置(configuration)。配置可以是很宏观的,首先,所有玩家其实都处在一个制度配置当中,比如游戏产业是在一个市场逻辑下生产出来的,同时又是在国家这套制度规范之下生产出来的,所以,不管你怎么去玩,都逃脱不了这些相对宏观的制度性配置。
第二种配置我称为技术配置。比如说你玩王者荣耀,你要有个智能手机,你要接入互联网,你需要掌握一些列关于软件运用和身体支配的技术规范,才有可能进入到这个游戏当中。它还涉及到游戏的设计、视觉化呈现,包括你们刚才谈到的游戏角色问题,其实都属于技术配置的一部分。
技术配置的实质是什么?实质就是一套规则,它规定了你应该怎么玩、怎么互动、怎么去和其中的故事元素进行对话、如何在游戏规则所确立的荣誉秩序中去定位自己的位置。我们在玩的时候,又应该如何调配自己的感觉系统、怎么去调动自己的身体?我们不能忽略这些东西,研究者不能只看玩家是怎么玩的,同时要看他是在什么条件之下玩。
第二个方面,当然就是要回到“玩”本身。我认为,“沉浸”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焦点。所以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在玩家的整个身体经验上,也就是所谓的具身性。我举个例子,在玩家与游戏互动的时间性关系中,有一个投资问题或时间经济学的问题。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玩家,时间积累得多了,你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等级越来越高,你在游戏设计的这套技术系统当中,你的名誉也会不断上升,这实际上是经济学逻辑。因为你投入了大量的身体体验和情感积累,时间可能过的会非常快。玩了多半天,我们感觉就好像只有几分钟时间。在沉浸之中,时间是高度压缩的。不过,当你回到现实世界当中,你发现自己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时,你对这个游戏的依赖性和时间投入更多了,让你不愿意放弃在虚拟空间所投资的情感、经验和时间,这显然是一个“玩”的路径依赖或者游戏实践的经济秩序问题。

周逵:我接着典林的说。他说的配置,除了技术配置以外,我也可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回到文本,因为任何玩家在游戏中的实践,都是在一个文本框架之中完成的,这也是一种世界观的框架。
你可以观察中国的这一类游戏是如何建构世界观的。现在所有的流行文化文本,本质上都在推行一个世界观。比如说我可以去研究王者荣耀,它的顶层是王道政治、天下主义、江湖义气还是新天下主义?许纪霖谈过新天下主义,我觉得很多文章可以拿过来投射,这种投射是很有意思的。
另外一个你刚才讲的对于时间的投入,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其实关于游戏成瘾我们今天没聊到。现在有很多游戏的什么青少年模式的成瘾机制管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除了硬性的要求多少小时下线以外,在游戏机制上,只要对这个人玩游戏的边际效用已经非常微弱时,他就自动放弃玩这个游戏了。比如说我每次玩游戏最后放弃,就是因为被我坑的实在是太冤,给我匹配5个全是射手,我就去睡觉了。这种匹配机制其实是更好的通过这种边际效用递减或者是直接断崖式的下降,来拒绝让一些人一直玩下去。

反过来讲游戏,我特别认同黄典林说的,不仅仅要研究players,还要研究游戏的人所处的情境。你刚才说text-in-use,我觉得这是player in-context。我一直很感兴趣,为什么王者荣耀大概有一半的玩家都是女玩家。要知道,我们小时候偷偷跑去黑网吧,这个场景中几乎是没有女生的,是完全男性主导的。
以前,女性其实是被排除在游戏的电子游戏场之外,但是现在因为移动游戏兴起以后,你会发现大量的女性玩家开始介入进来,女性玩家的声音越来越强,她们成为塑造、建构游戏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声音来源。这部分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考量。
除此之外,最近我看了一篇研究游戏代练的文章。十几年前就有人研究金币农夫的,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叫游戏陪练。比如有一个叫比心的APP,你上去你可以花几块钱,请一个人陪你一块玩。代练是我把我的账号给你,跟我玩,尤其是在欧美,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然后亚洲玩家帮他代玩;我觉得这里面有一半是为了兴趣、一半是为了工作,所以谈到那个词叫玩乐劳动(playbor),已经非常弥散化。它的形态、它的目的、它的边界其实已经不被传统的这种空间情景和场域所限定,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现在去重新去审视的。
董晨宇:周逵老师刚才提到成瘾这个问题。现在有大量研究关注青少年游戏成瘾问题,但很多研究里,其实是没有青少年的声音的,他们只是一堆数据。我很喜欢danah boyd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对于成瘾这个词本身怀有一些认识上的执念。
比如我们可以思考:成瘾这个事情一定是一个坏事吗?在很多情况下,可能是坏事,但你把成瘾换一个角度来想,这是什么呢?这叫心流(flow)。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尤其玩嗨的时候,会发现时间过得特别快,就说这就是心流。对于音乐家、演员、运动员、作家,心流是他们必须要锻炼的一种素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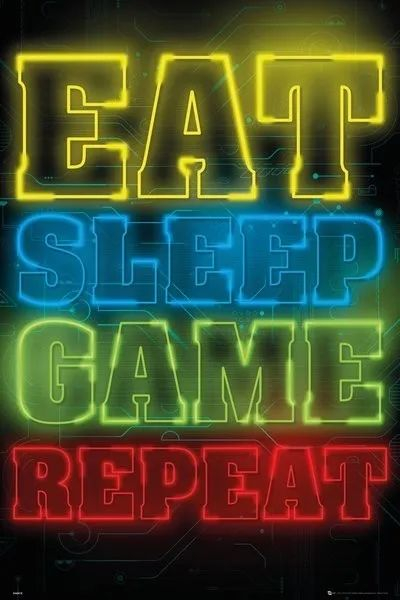
我们对于青少年打游戏的理解可能是不够全面的。我自己会接触一些中学生,我发现青少年的生活是高度结构化的。在学校里老师安排、回家之后家长安排。在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秩序当中,他们是非常需要弹性的社交空间的。
boyd也曾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孩子们是骑车上学,特别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路上碰到同学一块骑。这一路上的聊天,其实非常弹性的社交。我在人大工作,每天到了下午的时候,人大附中门口就堵得很厉害,都是接孩子的家长,把自己的车子停在路边。当然,家长是为了孩子的安全考虑,但其实,他们也压缩了孩子本来就不多的弹性社交空间。此时,社交媒体也好、游戏也好,就成为了这种弹性社交空间的一个新的出口。
04.给游戏研究入门者的建议

黄典林:游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文化现象,它是多面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研究它,当然不要求全,也不要说面面俱到,但是能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视角,无论是传统的文化研究或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还是以游戏实践本体作为研究对象的游戏学视角,都可以,关键是要能把握住真正有价值的问题。
第二,个人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可能是有偏见的。我们的偏见可能会限制我们的理解的维度,这是要处理好的一个关系,就是作为玩家的参与者和研究者之间的身份关系。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一方面我要去理解它,我要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但另一方面,当我们去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是要有一定的跳出来的能力,平衡好玩家和研究者之间的角色关系。
周逵:我接着黄老师的说。我们如果要从事游戏研究的话,有两种身份不要弄混,一个是玩家身份,一个是研究者身份。不要表面上在做田野,实际上就玩了一个晚上。我觉得处理好这两个身份,就要保持和游戏的一定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ing)。
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你作为一个玩家是有局限性的,玩家的游戏体验是非常主观的,它是个人游戏使用习惯的结果,有些人玩游戏,就死盯着一种玩法,他不去体验其他玩法。不过,当你转变身份,作为一个做田野的人进入其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是一种鼓励。他会鼓励我自己跳出舒适区。
之前章戈浩老师说,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我的田野,但是他会鼓励跳出你原有行为模式的舒适区,去让你去研究那些你所不了解的东西,比如说我以前,我打死也不会去比心APP上找一个陪练一块玩,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角度、敏感性或好奇心的时候,有的时候反过来也会丰富我们的游戏体验,或者是对于环境的认知。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重点,要处理好游戏研究和整个社会学研究、传播学研究的关系。你的论文不是游戏攻略,大多数时候是给non-player评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越是新的东西,你去研究它时,越要用保守的方法。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你研究本身的合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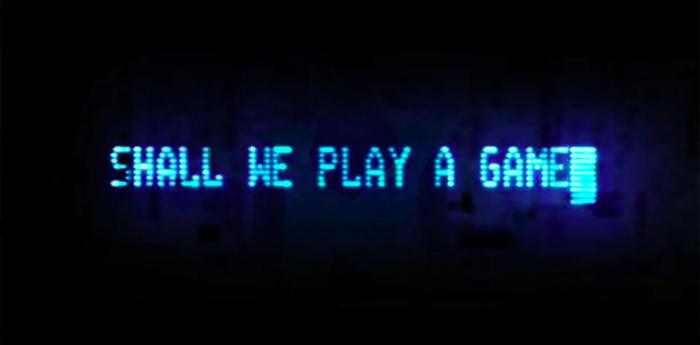
董晨宇:我接着周逵继续说。第一,我很同意田野的身份问题。现在很多学生喜欢研究游戏,因为这个东西和他们的生活很接近,而且认为这个研究过程是很愉快的,不就是打游戏吗?这种自己骗自己的情况,和看美剧学英语没有什么本质不同。我想说的是,田野方法是有一套的行动路线的,大家都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一直保持愉悦是不可能的。
我再回应一下周老师说的另一点,我也特别有感触。游戏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经常会有人在写文献综述时说,我没有找到我对这个问题任何之前的研究文献。去年有一位研究者在Game Studies上发了一篇文章,内容是“给游戏研究玩家的10个攻略”。他就说,千万不要说之前没有这个问题的研究。如果没有这类研究,99%的原因是这个东西不值得研究。如果你真的没有找到文献,你要说我没有找到,不能说没有。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论文评审也许能找到。
原标题:《当我们谈论王者荣耀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