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真正的马雅可夫斯基传记出现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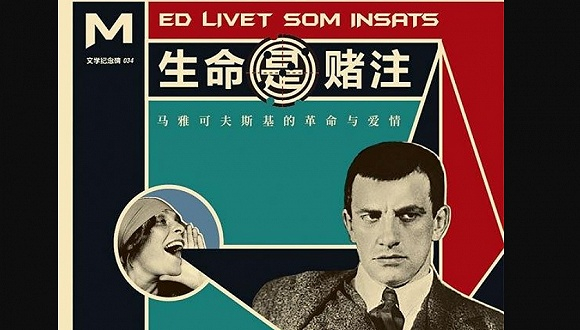
《生命是赌注: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与爱情》封面
五月初,瑞典著名传记作家,权威的马雅可夫斯基研究者,本特·扬费尔德(Bengt Jangfeldt)的《生命是赌注: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与爱情》的中文译本问世。这个优质的中文版由糜绪洋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扬费尔德总结以往马雅可夫斯基研究状况的时候说:“马雅可夫斯基却至今没有一本真正的传记。”那么当我们读完这本厚实的大作,掩卷而思:我们终于迎来了一本真正的马氏传记吗?
这本新的传记,以马氏的“革命与爱情”作为它的副标题。据糜绪洋,这本书的瑞典语原版,题名为《生命是赌注: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圈子的故事》。无论是原标题,还是中文标题,都准确地反映了本书的主要内容。作者将马雅可夫斯基和莉莉·布里克、奥西普·布里克组成的三人家庭作为核心描写对象。一方面,作者展示了马氏和众多女性的情爱纠葛。在这纠葛之中,莉莉是马氏终生的真爱,是马氏诗歌的缪斯女神。另一方面,作者描绘了以三人家庭为核心的先锋派艺术圈子。这个朋友圈子由众多文艺巨擘和理论天才组成。十月革命之后,马雅可夫斯基全身心拥抱革命,为了使自己的创作适合苏联群众的需要而挣扎苦斗。
应该指明,在革命与爱情两个主题中,后者占据了更多篇幅。这是本书的主要特色。莉莉·布里克是一个不羁的女性解放先锋、一个性自由的实践者。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激进主义中,恋爱和婚姻自由就是一个重要命题。而到了布尔什维年代,由于共产主义对于平等的诉求,由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力地论述了婚姻制度是私有制的一种形式,是男性对女性的占有,于是婚姻制度受到极大的挑战。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马雅可夫斯基进入莉莉·布里克和奥西普·布里克夫妇的生活中,组成一个三人家庭,这并非奇闻怪谈。他们的关系,反而是新伦理的一种范例。
马氏和莉莉在精神上的依恋关系,一直持续到马氏自杀。他们并不束缚对方,并不阻挠对方发展新的爱情关系。本书将更多的篇幅放在了讲述这一段段情爱轶闻上。在马氏自杀五年后,斯大林为诗人认证:“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领袖的评价,立即抬升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地位,他成了苏联精神中的一座纪念碑。由于被认证为苏维埃的代表诗人,于是他的创作必须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范。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中未来主义的成分被删减、弱化。而他和莉莉的关系,也在后来被看作不符合苏联价值观,于是人们将莉莉从马氏生命中删除了。
扬费尔德对于马氏和莉莉爱情的重新强调,也正因此而意义非凡。因为找到了马氏的真正缪斯,这将引起对马氏创作的重新评估。扬费尔德是马氏专家,他掌握巨量的一手文献,这使得这本传记具有十足的权威性和重要性。然而,正是因为极度重视描绘马氏爱情史,这阻碍了本书在其他方面,成为一本有力的传记。
尼采认为,以往一切伟大哲学作品,都是“其作者的个人坦白,都是一种无意识的、未被注意到的传记”。要理解康德其人,阅读《纯粹理性批判》要比阅读任何一本康德传记都更有用。对于诗人来说,这个法则或许更加正确。《生命是赌注》花了那么多笔墨在马氏爱情轶闻上,而却没有花同等或更多的笔墨,进入马氏作品。可是不见其诗,如何能望见马氏其人、其精神?马氏每一段情爱的前因后果、他的圈子怎么彻夜打牌和麻将、莉莉托付给马氏的购物清单是什么,了解这些,固然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些人和他们的时代。但是,所有这些对于理解马雅可夫斯基,都只具备次等的重要性。
要了解他,必须到他的作品中去。扬费尔德在作品分析方面,花费的精力太少。而且当他分析作品时,仅仅局限在介绍这些诗为何诞生,以及它们主要讲了什么。研究马氏,难道可以免去对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介绍?难道可以忽略马氏在韵脚、节奏、造词、声响方面的创新?难道可以无视马氏诗歌中澎湃涌动的现实要素?还有,马氏在电影和戏剧领域的探索,他和梅耶荷德传奇的合作,这些不值得花费笔墨吗?
缺少了对作品的详细关照,马氏的真正精神形象,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卢那察尔斯基惊叹马氏是一个“巨大的诗人”。扬费尔德引述了这个表达。可是在他这本书中,除了马氏一米九的巨大身材外,我们找不到巨大的诗人在哪里。
扬费尔德并非在这些方面没有造诣。例如,他的论著《马雅可夫斯基和未来主义 1917—1921》(Majakovskij and Futurism 1917-1921)已经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这里就有更多作品讨论。我理解,这些东西也许本就不在扬费尔德的写作计划里。他的目标或许只是拨开围绕马氏生活的迷雾,他也已经完全地做到了这一点。只是作为读者,因为在这本期待已久的传记中,找不到诗人之精神的踪影,不免感到遗憾。这个遗憾,使得人们在面对“一本真正的马氏传记出现了吗”这个问题时,踌躇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