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数字时代,我们何以成为“网中人”?—— 读《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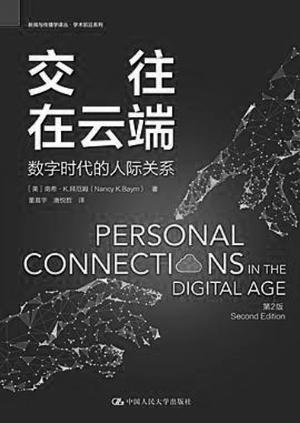 《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
《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美) 南希·K.拜厄姆 著
董晨宇 唐悦哲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1月出版
⊙林颐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认为文字会破坏口述传统、落在纸上的都不是真理。后来,随着印刷术发明,古老的记忆之术失去了用武之地。再后来,电话、电报、广播、电视等传播技术的发明,不断打破人类社交的时空界限。而今,进入互联网时代,我们拥有了电子邮件、移动电话、短信、即时通信、网聊、留言板、社交网络、照片分享、视频分享、多人在线游戏等诸多新型交往方式。这个世界更新得实在太快,快到让我们感到不安。
难怪《交往在云端》开篇即言:“在理解数字媒体的性能及其社会影响的道路上,我们正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时期。”该书围绕数字媒体和数字设备在人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展开,旨在为大家提供一种批判性思考的方式。作者南希·K.拜厄姆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传播学教授,现任微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参与创立互联网研究者协会并曾担任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传播、新媒体和粉丝文化。她认为,不管这些新技术带来了什么样的破坏或者形成了什么样的结构链条,它们都会深刻影响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社区、关系和自我。
今天,我们在微博、脸书、推特或其他的互联网平台上发布、转发一些支持或批评的文章,或者对一些言论进行点赞、截图,在各种媒体所组建的社交环境中,这些信息沿着网路在人群当中流传,这个速度比古典时代的广场演讲和抄本传递要迅速得多,但本质是一样的。南希认为:“从远古时代起,这些传播技术出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能让人们在身体缺席时,仍旧能够传递信息。”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更加公正,对今天的理解更加清晰。新技术之所以让我们感到焦虑,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于未知事物的本能畏惧,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对待技术的立场,启动了人们对于信任、联系、保护与自我保护的深层需求。
每天,来自全球各地数以亿计的人,在线上同步或异步分享兴趣爱好、扮演角色,并在线上结成了群组和“虚拟社区”。作者考察了线上社区的共享性实践。比如,她认为“潜水者”也是一种珍贵的线上参与模式,可以被理解为倾听。相比之下,作者更关心的是共享性的空间感、共享性的实践仪式和社会支持的交换,是如何有助于在数字环境中形成社交感。情感支持、自尊支持、信息支持,具有循环性和自我强化性。深植于我们头脑的个人经验、总体文化,或者与大众媒介的接触,都可能影响个体对某个议题的感知程度,从而促使个体参与社区建设,并构建自身的网络形象。
为此,南希做了“社会临场感”和“线索滤除”方面的研究。社会临场感是指“在人际互动和关系中,交流对象的显著性程度,以及主观感知的亲密性和直接性。”在互联网中,因为社会身份线索隐晦,交流者的性别、种族、地位、外貌和其他公共身份特征都无法一眼就能辨识,匿名程度相对较高。去个人化的环境、中介化和匿名性都会导致社会权力的再分配和情感表达方式的多样化。人们在媒体上交流的方式塑造了媒体本身,也重塑了个体自身。
作者认为,人们在网上建立关系时,身份是最被关注的问题。没人敢说他的网上形象和现实中的角色完全一致,我们的个性化自我与我们的社会化自我之间多少会存在一些差异。我们在网络情境中向他人呈现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方式,暗示或引导他人对自己形成的印象,以及维持这种印象时,都会与现实层面进行分割、修饰和表演。正如作者所说,当人们建构线上信息时,他们需要依靠想象的受众,即“内心对交流对象的概念化”。由于想象的自我和实际自我、想象的受众和实际受众之间往往存在差距,有时候就会造成坍塌。
这个问题也涉及隐私,我们很难估计自己在多大范围内进行了自我暴露。作者从网名、自拍、头像、言论、好友列表等角度剖析了身份信号线索对网络用户人格特质的呈现。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关心网友的社会身份,线上社交大多始于共同的兴趣或经历,以及对方吸引我们的品质。一种可能的隐匿、发现、虚假现实、再发现的无限循环,决定了网友的交往亲密度和关系发展。数字媒体似乎把自我和身体截然分开,造就了一种仅仅存在于展示中的无实体身份,但是自我和身体归根结底仍然是一致的。交流过程的信息不对称性允许我们营造自我但并非伪造自我。
所有的媒介文化发展都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人类的交流中,人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缺席。电话延伸了我们的耳朵,照相机延伸了我们的眼睛,而互联网呢?在它的世界中,一切信息的源头仿佛都深藏不露,然而又脆弱不堪,随时可以风化在所有看客的窥视与唾沫里。南希对于网上自我的呈现方式的重点论述,表明了她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作者的很多看法都极有见地。比如,在有关网络社交与地理空间、文化空间相联系的讨论中,作者指出了社交媒体影响公众对社会与政治议题关注的效果。的确,从前我们只能通过报纸或者电视了解时事。而现在,人们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和朋友圈,一次又一次的自发筛选与推送信息,很多人已经渐渐习惯于用社交媒体的交流去了解动态、观察事件、组织议程,并且影响舆论导向。
在这个春天,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我们隔着口罩、隔着网络,在尽量避免面对面接触的极端条件下,我们如何传递温暖的情感,触达彼此的心灵呢?在根本上,网络社交可能是现实社交的萌芽,现实社交也可能是网络社交的延伸,我们在“云端”伸出手指的每一个瞬间,都在重塑我们的互联网环境,也在重塑我们的社会环境,线上线下相互依存,也相互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