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华兹华斯诞辰250周年:心灵的序曲和不朽的俗子
华兹华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被认为是“湖畔派”三诗人中成就最高者。他的诗句“朴素生活,高尚思考”对读者影响至今。今天是这位诗人250周年诞辰,本文追溯至他早年生活经历,并论及他诸多诗歌写作理念。
撰稿 | 后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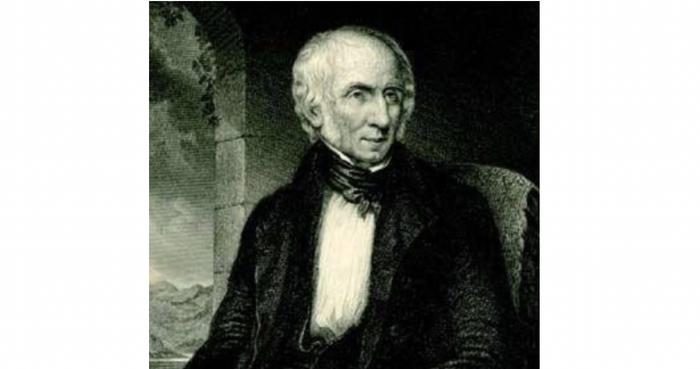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年4月7日-1850年4月23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品包括《抒情歌谣集》《丁登寺旁》《序曲》《她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等。
威廉:成为华兹华斯“之前”
1770年4月7日,英格兰坎伯兰郡
(后来归属于坎布里亚郡)
湖区德文特河畔的一个律师家庭迎来了第二个儿子威廉,次年是女儿多萝西。父亲约翰热爱文学,他把自己的藏书对子女开放,督促他们在《天方夜谭》、莎士比亚、斯宾塞中寻找自己的心仪。孩子们,尤其是威廉和多萝西常常结伴去海边玩耍,光着身子戏水玩石。威廉后来回忆说,“当妹妹初次听到海涛拍岸的声音,看见波澜起伏的海景时,她被感动得潸然泪下”。威廉何尝不是呢?
当时瓦特的蒸汽机刚申上专利不久,人们只能用脚步和马车连缀起湖区上的不同地点。威廉便在湖区闲步,常常跋涉数里,也因此他的腿发育得不体面。德昆西在初遇威廉就诙谐地记下了一笔,“我跟任何一个冷眼旁观的女人想的一样——只可惜他没有另外两条出色的腿,能在没有靴子遮盖的时候,出现在宴会上!”借着这双腿,威廉一次次远游,他流连在德温湖,游荡在埃斯威特湖,玩味在康尼斯顿湖……温特米尔湖……格拉斯米尔湖……罗德尔瀑布……达登河……

《格拉斯米尔日记》,[英]多萝西·华兹华斯著,倪庆饩译,花城出版社,2011年8月。多萝西记载了随兄长一起定居于格拉斯米尔三年多的生活,直到威廉·华兹华斯结婚后日记中断。
某个夏夜,威廉解开小舟,独自划向埃斯威特湖心。在暗中,他忍受着来自山间回响,提防着内心的不安,用力摇动桨叶,用双桨“猛击无言的湖水”,小舟像只天鹅向一处山峰漂游。山峰“那阴郁的形状在我与繁星间/愈加增大着它的神曲,而且/随着我的划动向我逼近,就像/活的东西,有动作节奏和自己的/目的。”被自然之重垮下来的威廉把小舟调转,凭天光,参照着黑峰,回到岸边,沉郁地赶回了家。之后几日,他被“无物的空寂,或茫茫废墟”吞没了思绪,那“巨大超凡的形状”干扰他的生活。他认知和揣摩到了自然了吗?他可以像《序曲》中所写的那样懂得“靠崇高的/事物,靠永存的客体……痛苦和恐惧变得/圣洁,直至我们在人心的跳动中/发现一个宏伟壮丽的含义”吗?他又如何从威廉变身成华兹华斯呢?
请允许我们先在华氏的经行处做一次朝圣。华氏于1835年出版的《湖区指南》
(可能是华氏生前最畅销的作品)
为游客做了一次地形学描写,也为我们“提供了心灵的指南或向导”。此书的讲述口吻将作者的古老气息和绅士风度暴露无疑,“要欣赏温德米尔美景,最好既站在岸边又游荡在湖面……温德米尔有广阔的湖面、众多的小岛、源头的两个溪谷以及溪谷周围雄壮的山峦……你最好找一个月明星稀的宁静之夜去…… 夜航之旅的最后,你可不要忘记观赏那广袤的湖水和静静地汇入湖水的河水。那河水安静地流淌着,好像不是流自峻峭的溪谷或暴涨的山洪,而是宁静的湖水流出去似的”。
这本旅游小册子晚了托马斯·威斯特的小册子半个世纪,彼时刮起了旅游热潮,笛福和托马斯·格雷都曾踏足湖区,格雷赞美拉斯米尔是“毋庸置疑的小天堂”,又称湖区“没有半片的红砖绿瓦、没有俗丽的绅士屋宇院墙来侵扰这片意外天堂的静谧;只有宁静,质朴,知足的贫困,以及最简洁最得当的装扮”。人们追踪着时兴的园艺的潮流和旅游的潮流,完全不在意脚下留下的脏东西。
及至华氏写《湖区指南》的时候,湖区已经大为变貌,人们蜂拥而至,甚至定居在此,风景在侵占中显得面目全非。华氏写道,“在人们现在更常光顾的地方,几乎每一转身,触目可及的便是那些不协调的僭越之物,它们正破坏着那些被愉快地保存了数个世纪的自然景致布局和色彩的静谧和谐,没有谁能对此视而不怒”。他还给《晨报》写信,指责铁路入侵带来了速度、噪音、黑烟和人群。为了整顿湖区,他在《湖区指南》中提出,参照威廉·吉尔平的“画境”学说,对湖区的环境和民居进行重缮,去除暴露,依从自然。他还希望人们可以认识到“湖区是国家财产,我们每个人都有权用眼睛欣赏她的美,用心灵感受她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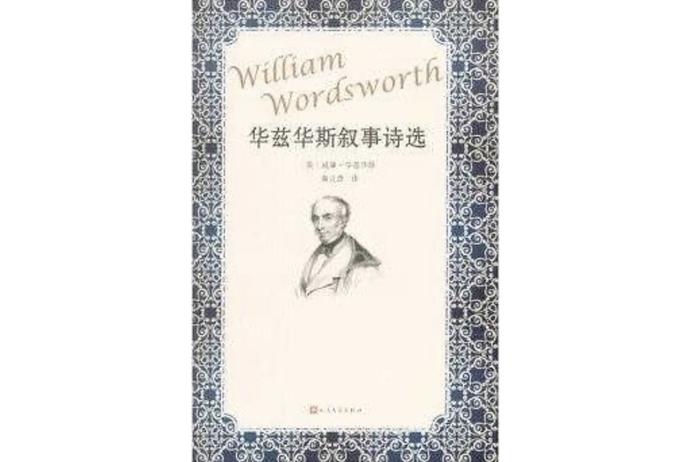
《华兹华斯叙事诗选》,[英]威廉·华兹华斯著,秦立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6月
踏上文学之路
时间回到威廉的少年时代。母亲逝世后的次年,威廉被送到豪克斯海德学校就读,直到他离开这里就读于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其间,威廉的父亲也在他13岁时病逝了,柔情馥郁的多萝西在后来的信中说,“多少次,我和哥哥一起抱头痛哭,那是多么辛酸的泪水。日复一日,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失去双亲意味着什么”。
豪克斯海德学校建立于1585年,这所文法学校由一百名男孩和四五个老师构成,它在古典课程和现代课程上都是最好的学校之一,而因为靠近苏格兰,它又得以参与北方文艺复兴。威廉的课程成绩无疑是好的。一个老师记录下了这样一个事情:下课后,教师仅剩威廉一人,他走近发现他正在阅读牛顿《光学》,一个小时后他仍在读,等老师离开教室后再回来,威廉就拿着书问他是否可以先保留这本书直到他看完。威廉从豪克斯海德学校学到了精湛的语法、修辞学以及更为重要的“文学的自然”,前者是他从大众教育所受益的部分,后者让他走得更远。他热爱维吉尔,雄心勃勃地为翻译《埃涅阿斯纪》做着准备。

《作为听者的华兹华斯》,朱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
从剑桥毕业的威廉·泰勒是小威廉走向文学之路的关键人物,他从1782年直到1786年逝世为这所学校的校长。在逝世前,他将男孩们延揽到床边,一一传话,泰勒对威廉说,“我的头颅很快/会躺在土中”,这个祝福正见泰勒对威廉的引导和祝福。生前,泰勒指导阅读晚近的和在世的作品:爱德华·杨格、托马斯·格雷,苏格兰复兴中的托马斯·帕西、罗伯特·彭斯,对贫民抱有同情和关怀的乔治·克拉布、约翰·兰霍恩、威廉·申斯顿。没有人知道这些诗人有哪一位走得更远,他们通常被视为次要的诗人,他们独立在英雄双韵体之外,构成了一个必要且持续的传统。
就我们所知道的,威廉也没有走出这个受惠于泰勒的课程或者系统,此后威廉用他的对于自然和心灵的爱发扬了这个系统。成年的威廉再次来到泰勒的墓前回顾了这段历史,“可靠的向导,卧床说完临终的/告诫……他热爱诗人,当我/依从他的意志,开始辛勤地/编织我最初的歌谣,他对我产生/殷切的希望;今天他若活着,/定会喜欢我,认定我并非没有/出息,也未违背他的意愿。”
“大约十岁时,我的心灵开始/有意识地享受如歌的语言织体,/追求文字本身的甜美——一种/纠缠,一种智能;一些词语/被我选中,只因有趣、华丽/或让我痴迷。”在他的作品和回忆录里,威廉历数了这个时期他沉浸的文学:《荷马史诗》《天方夜谭》、莎士比亚、弥尔顿,最重要的还有被笼统地称作感伤主义的作品,菲尔丁、《堂吉诃德》《爱弥尔》《吉尔·布拉斯》《格列佛游记》、欧西安
(莪相)
……威廉称伟大的作品是一种伟力,“仅逊于大自然的力量”。他的忘我将他领入梦境,梦中阿拉伯人带来了石头和贝壳,一个能以最纯的理性契约使人与人产生关联,一个能超越所有风的呼唤,振奋我们的精神。醒来的威廉怀里正抱着塞万提斯的“游侠史传”。就这样,少年威廉在划船和漫步中,再也无法在文字中将幻想和现实分开,一切都似真似幻,他“看见每一滴智慧的/雨水落入心灵的水桶”。

华兹华斯碑文局部。
无法归类的“浪漫主义”
由詹姆斯·麦克弗森杜撰的诗人莪相是不得不提及的。在修订版的《序曲》中,他提及了莪相,“还有从莫尔文召来的/欧西安
(别不相信,这可是纯正的/事实)
”。然而在《抒情歌谣集》1815版中他却对莪相颇为讥讽,“奥西恩
(莪相)
这个幽魂脱胎于一位无耻的高地人,他温情地拥抱传统的阴暗面”。
威廉对风靡欧洲、受到广泛赞许的莪相并不以为然,他否定莪相对各国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具体的影响,“没有哪位作家胆敢涉险在形式上去模仿这些诗歌,哪怕以最不起眼的方式,只有那个孩子——查特顿例外”。威廉的宣言产生了一定的效力,有的学者便采纳了这个说法。雷纳·韦勒克提出了质疑,他把上述的双重话语归因于他试图和深受感染的民歌内涵保持某种距离。当然,《爱丁堡评论》编辑杰弗里贬低威廉而褒奖莪相的行径也让他无法平静地看待他对莪相的接纳和学习。虽然威廉的态度几番起伏,但是他似乎从未怀疑过莪相的原创性,从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知道,莪相必然是威廉的导师。他们的创作都指向了感觉、情感和想象,而这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布鲁姆的“民主时代”。
不妨从中国的引介出发去理解华兹华斯的民主问题。1949年,国内的《文艺报》刊文《开讲英国诗想到的一些体验》,其中说到“英国浪漫诗人或多或少是革命的,都觉得为自己也就是为人类争自由。……他们要求自由,可是愈干只有离目标愈远。他们愈成熟愈疏远他们年轻时候的理想。他们逃避了现实。……渥茨渥斯
(华兹华斯)
不再指望以反抗争自由,本来小有收入的,也就悠然地‘回到自然’”。自此,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三位湖畔派诗人便被定调为“消极的浪漫主义”。依照范存忠的说法,中国文艺界所遵从的是拜伦和雪莱的和现实主义结合的浪漫主义。
1978年,王佐良对消极浪漫主义的定调进行纠正,称华兹华斯的逃避乃是因为对拿破仑战争的失望。《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也把主线设定在华兹华斯的民主追求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王佐良甚至将华兹华斯的写作史和法国大革命连接在一起,“1796年到1806年的收获是因为法国革命给了他真实的激动,而激动是从生活里来的,所以有印象可写,有感受可谈,而一旦对这一切只有憎厌,那么生活的贫乏必然最终要导致创作的贫乏。”从1807年起,华兹华斯的诗歌生命无可挽回地衰微了,曾经的弥尔顿退化成庸人,他也开始敌视英国民主运动,最后王佐良盖棺论定道,“这是一种从纯真的童年和热情的青年的倒退和僵化,是‘幻觉的闪光’的消失,是‘时间之点’的隐藏,蒙受这全部结果的是英国浪漫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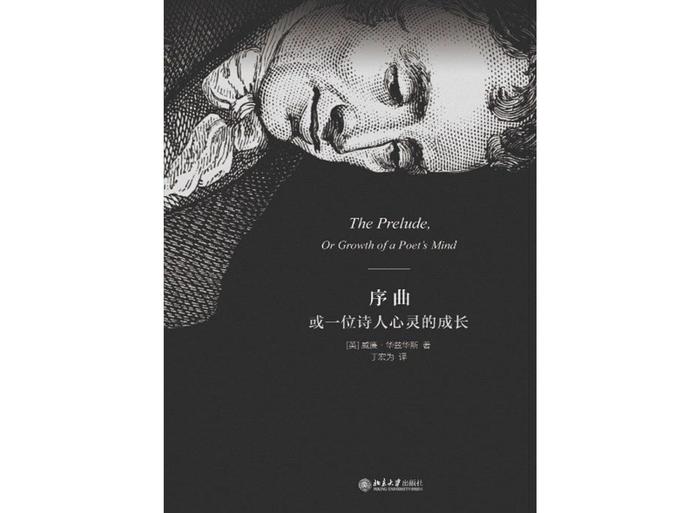
《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英] 威廉·华兹华斯著,丁宏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
华兹华斯的诗歌终究无法限定在某种层面的浪漫主义之上。华兹华斯可以是陆志韦的吊古伤怀与同情人民,可以是《中国人的精神》中的宁静祥和的中国范,可以是胡适的解放语言和文体,可以是田汉的劳作,可以是《沉沦》捧读其诗的在危机中摇摆的乡间漫步者,可以是徐志摩的见小花而泪而哭的纯粹艺术,可以是吴宓的对于古典主义美学的追求,可以是朱光潜的从主观经验中跳脱的诗学经验。不单华兹华斯无法定义,浪漫主义也无法定义。整体来说,浪漫主义是一个局面,这个局面既有对生命的渴望又有对死亡的垂涎,既有为艺术而艺术又有拯救社会,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既有精确又有模糊。即使我们为浪漫主义取了一个平均,我们也还是无法衡量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值。我们不能简单定义一个文学生命体强弱和盛衰,我们只能在诸多社会的文学的纬度中观察到他模糊的面向和轮廓。
不同于德国浪漫主义的先行和哲学诗学背景,英国浪漫主义在推进、诗学、革命等方面都要薄弱很多。英国浪漫主义特殊与必然体现在爱大自然和沉思大自然上。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柯勒律治有鸦片瘾、好幻想,骚塞做职业文人、爱虚构,拜伦恶魔般地追逐革命,雪莱自由崇高,济慈卑微而丰满。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是山水之交,有胶漆时也有分裂时;他的命途和骚塞相仿,人生越走越保守;他又为拜伦、雪莱和济慈所不齿或敬仰;总之,他最长寿,几乎最保守,也最爱现实的大自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就缔造于这六位友人,他们彼此间错综联系,有共居、有交游、有罅隙、有合作、有祭祷,一举用浪漫主义建造了彼时的英国诗歌高台。
出版于1798年的《抒情歌谣集》是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双人舞,书中收录华兹华斯包含《丁登寺》在内的19首诗歌,柯勒律治包含《古舟子咏》在内的4首诗歌。此书的销售状况很不好,评论界一片骂声,人们也远远没有像哈兹里特那样“感觉接触到一片新鲜的土壤”。此书失败之处在于两位诗人的大自然歌咏和现实的内容和当时的诗歌潮流太不一样。有鉴于此,华兹华斯为1800年的再版写了一个序,表明他之赋予情感以重要性,普通语言的必要,其中“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更是千年诗学中少有的原理型的佳句。
对他所强调的这两条,中国读者都有颇深的误解:其一,情感并非当下语境中的情感,而应属于古典主义范畴,它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某种现代变形,它强调灵魂浸染、心绪逐物;其二,他所提的普通语言应是一种普遍语法,它能够承载散文和诗歌两种不同的实质,这种普遍语法给诗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必须活泛热情、通晓人性、拥有开阔的灵魂。1814年发表《漫游》后,《爱丁堡评论》对华兹华斯大加挞伐,称其“用高雅的风格描写一位四处兜售绒布和手帕的小贩,必将吓跑他的客人”。次年,他为《抒情歌谣集》的序言再次做了补充,反复论说想象力之美,“想象力也能造形和创造……想象力最擅长的是把众多合为单一,以及把单一分为众多”。言下之意,评论者并不懂得运用想象力,而只能运用自己那独裁的眼睛。不过,有关于想象力的论述还需要咨询柯勒律治,尽管华兹华斯认为它很肤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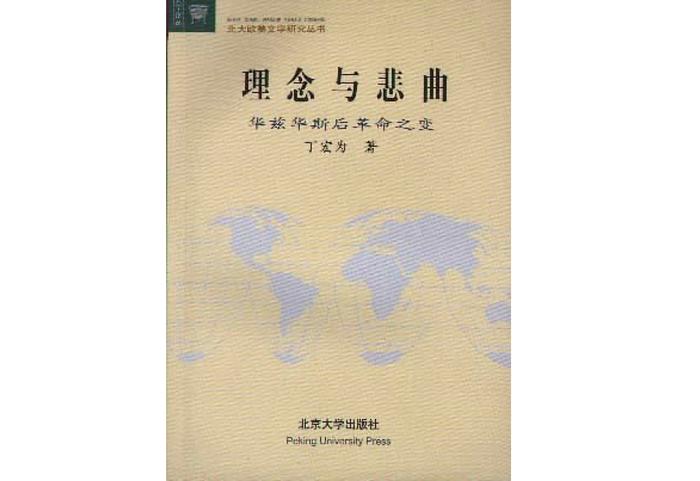
《理念与悲曲:华兹华斯后革命之变》,丁宏为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回到鸽舍
正是在1815年、诗人35岁这年,华兹华斯变了。他又回到了鸽舍,和妹妹多萝西过着“起居朴实、思想崇高”的生活。他不再是把全部的爱献给人民的民主派,他参加了保乡团,和英国同仇敌忾。他强调自己的英国公民身份,而英国性几乎是华兹华斯诗歌的一个隐秘而重要的主题。和青梅竹马的玛丽结婚后,他开始收敛自己,对家庭负责,渴望金钱。他的大弟弟约翰出海遭遇了船难,这令他把关注更多地迁移到家庭上。最亲爱的的朋友、他在诗歌中的另一个自己——柯勒律治离开后,华兹华斯与乔治·白蒙爵士、斯科特等文化界名宿交游甚多。诗人哀叹着,“我灵感的守护神如今在哪里?我的豪情、我的梦呢?”1798年萌生、几经修改的《序曲》在这年成稿了,它要等到诗人逝世后才能重见天日。一个鲜活的生命链条慢慢结束了,那些被保有的崇高、大自然、永恒追求、“全世界共有的心灵”重新回到它们所在的书籍和时空里渐渐沉寂。而浪漫主义文化和自然才刚刚在世界上被见证,人们相信着它,人们建构着它,人们将它延续着直到今日。
在他的田园诗、漫游诗、公民诗、致诗、十四行诗的背后,华兹华斯似乎自然地进入了一个特殊的位置:英国的公民诗人。通过殖民、战争、清教改革、领土融合、工业革命、民族运动、文学经典化,英国将自己和她的公民想象成一个大不列颠王国,而这个王国正代表着世界的方向。华兹华斯的诗歌正从转变中的英国和世界中取得了弥尔顿以及中世纪诗人们所不能取的维度。从这个角度看,1815年不再是一个转变的时刻,伪装的时刻,双面人的时刻,而是一个从诗人到公民诗人、从诗人到英语诗人、从诗人到世界诗人的时刻。他用他专一的诗歌实践完成了歌德的蓝图,他联合了浪漫和现实,联合了国族想象和浪漫诗歌
(田园诗)
,联合了想象
(力)
和清教经验
(中世纪基督教美学)
。《孤独的收割人》《在西敏寺桥上》《丁登寺》《漫游》可以说是这样一个整体世界的一部分。“多少次/在精神上我转向你,啊
(……)
/你这穿越树林而流的漫游者,/多少次我的精神转向了你!”当
(……)
填入代表英国的内容,华兹华斯就成为了那个读者最常感受到的华兹华斯。
最初、最后、中间、永恒
M. H. 艾布拉斯姆认为存在着两种华兹华斯。一种是人文主义的华兹华斯,他遵循简单、普遍、永久、内心的激情、伟大的感情、人类的存在、大自然。另一种是信奉复杂、悖论和奥秘的华兹华斯,他为未多表露的基督教传统引召,他在孤独中学会了谛听和躲避,他和诺瓦利斯是同流。
让我们再次回到他的Art《序曲》中。“我以如此方式/与天地间每一种被造物交流,看它们/以崇敬的表情和爱的目光注视着/造物的上帝。”这句话给M. H. 艾布拉斯姆一个清晰的答案,诗人两者都不是,两者也都是。在这句诗里,诗人旁观着生命和上帝的交流,他位于由诗人、生命和上帝组成的三角的最顶端,但这是一个如此谦卑和柔和的顶端,它并没有放大那个所谓的浪漫主义自我
(又一个杜撰的概念)
,它将“时间之点”、“无形的链环”和互联的法则播撒给每一个存在。
我们知道诗人追求的是“人们的热情与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的合而为一”,诗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如此。在诗人“心灵的长河”里,他用“心灵的眼睛”照见了“比四下里凡庸的外表更高超、更秀丽的/景象”,他用“辛劳/换得持久的赞美与光荣”以让“荣耀与知识产生威力”,他“在这/驳杂中漫游,兴趣盎然”。他是哈兹里特眼中的把握情感的天才,他是阿诺德眼中的是希腊遗骨,他是大自然眼中幸福的、被宠爱的孩子。如济慈所命名的“诗性人格”一般,华兹华斯不具有自我,同时又是一切;万物中最无诗意,因为他没有身份,同时又始终在塑造着……这并非是在褒扬诗人,这只是在描述诗人的诗歌宇宙。
最后,让我不无武断地说,华兹华斯的诗歌正像《启示录》“是永恒来世的象征与符号,属于最初、最后、中间、永恒”。
撰稿 | 后商
编辑 | 张进 罗东
校对 | 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