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他或许不是最后一个“扔”资源的纪录片导演
FIRST青年电影展 凹凸镜DOC
中国的纪录片导演,能够期望什么?
蒋能杰期望的,只是他的片子被看到。他守在《矿民、马夫、尘肺病》的豆瓣页面,谁点一个“想看”,就把资源私信过去。
纪录片境况的惨淡和边缘,在这个导演亲自驻守的豆瓣页面,露出冰山一角。

几天之内标记4万多人想看,5千多人看过
这个生态也是脆弱的。病毒肆虐之下,国内外各大影展取消和延期,纪录片本就稀缺的放映机会骤然减少,抵达观众的通道越发逼仄。
蒋能杰导演的《矮婆》曾经入围12届FIRST影展的产业放映。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给网友发资源链接的纪录片导演。站在前途未卜、少人问津的路口,导演和他们的纪录片,该去往哪里?
01
入围电影节,我还是等不到一块大银幕
东楠想退出竞赛单元。
一个月前, 瑞士真实影展(Visions du Réel)传来消息:FIRST纪录片实验室项目,陈东楠导演的纪录片《旷野歌声》入围国际竞赛单元。

第三期FIRST纪录片实验室 纪录片项目《旷野歌声》
讲述了大山里一个合唱团的“前世今生”
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四月份,《旷野歌声》将在某个瑞士的影院举行世界首映。
然而入围消息公布没多久,疫情猛地击中世界各大电影节。东楠逐渐感到焦虑:“撞上这个混乱时刻做影片首发,真是太糟糕了。”
她的担忧很快应验。
《旷野歌声》的后期是在洛杉矶做的。早先国内疫情严峻,东楠去不成美国,线上沟通不像当面那样顺利。后来COVID-19在美国本土甚嚣尘上,在美的工作室有诸多不确定性。就这样《旷野歌声》的后期一拖再拖,要想赶在影展开始前交付成片,很悬。
当初拍完《旷野歌声》,东楠就对纪录片实验室的同事说:“放映这个事儿,我已经有点绝望了,不太想这个事儿。”2020年伊始入围影展的消息,不是没有带来早点见到观众的希望。但很快地,急转而下的国际电影市场局势,把她逼入更深的失落里:“世界都这样了,我觉得自己的片子不重要,所以没有信心继续做下去,也犹豫影展会不会如期举办。”
瑞士真实影展最终没有取消和延期,但不得不改成线上举行:在影展期间,观众可以通过影展官网在线收看影片。

线上电影节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东楠蓄力多年创作的纪录片,仅此一次的、最为瞩目的世界首映,将在每个人家里的笔记本电脑、甚至是手机上亮相。
“我为这部影片付出那么多,后期很仔细地调色和做声音,是为大屏幕做的,不是给笔记本电脑的。”

《旷野歌声》剧照
“没有一个导演会对此感到愉快。”
韩萌是第12届FIRST影展竞赛评审,这段时间,她导演的纪录片《遥望繁星》相继入围了包括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IDFA)主竞赛单元在内的五个国际影展。

《遥望繁星》剧照,该片聚焦环境问题
起初收到IDFA的入围邮件时,韩萌非常激动:“好啊,我想我要做新的片子了。”
随着她入围的瑞士真实影展和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CPH:DOX)纷纷改成线上举办,韩萌难掩担忧:“我就是按照大银幕来拍的,后期调色都是为了大银幕。”这和东楠的话如出一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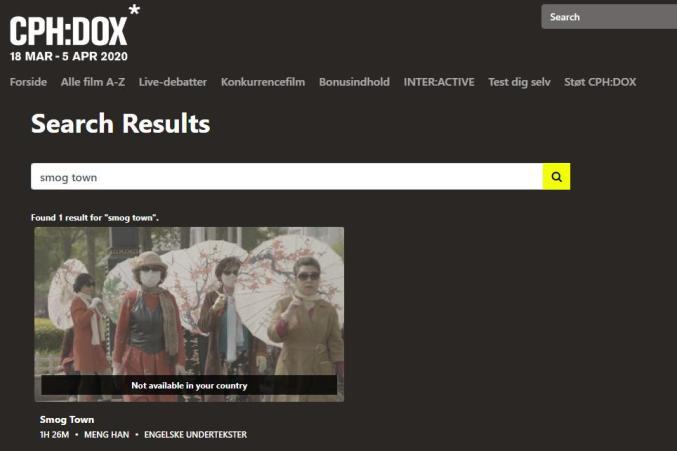
要不要在流媒体上放?韩萌异常坚持:绝对不考虑。她一方面期待影片能和观众交流互动,一方面出于保护影片主人公的心理,不希望受到大规模的关注。所以基于影院场景的影展成为了一个安全而精准的选择。
最令人担心的是影片安全问题。
《旷野歌声》有国内发行的计划,一旦影展的线上放映被盗录,盗版流传开来,“后面(国内发行)的事情就不太可能了。”
韩萌这几天一直和销售的同事沟通,虽然她对《遥望繁星》在国内上线不报太大希望,但她害怕盗版流传开后不可控因素增多。
综合考虑发行销售的风险,后期剪辑的压力,以及对属于自己的大银幕的等待,东楠最终决定撤片,放弃珍贵的国际竞赛单元角逐机会。
韩萌笑着说顺其自然,参不参加都不重要:“片子是拍给历史的,拍给未来的,是过去的一段证据。即使失去了参与电影节交流的机会,相信好的片子,还是会在五年十年拿出来看。”
她们私下聊天,聊疫情平息后大家做一个“Lost Films of 2020 Festival” ,召集2020年入围影展却没办法被看到的电影,再给大家放一次。
02
扔影片资源是自救
对纪录片,电影院的准入门槛苛刻昂贵,上线流媒体恐怕是见到观众的最佳选择。既然早晚要上流媒体,为什么导演们偏偏对电影节线上放电影有抵触情绪?
东楠说:“如果上院线的机会少,那能在大屏幕上播的只有电影节。”
对她来说,无论如何,第一次得在大银幕放。
韩萌觉得电影节就是交流,通过电影跟关心这件事的人互动,网上播实现不了这些。

《旷野歌声》剧照
韩萌和东楠,这样能够入围重要影展主竞赛的纪录片导演,尚且对影片能否见到观众焦虑和不安。大量的纪录片导演都蛰伏和沉寂着。《矿民、马夫、尘肺病》的“一夜爆红”撕开了现实,创作者为守住影片的完整性勉力支撑,而“被看到”从来不是一件板上钉钉的容易事。
为了被观众看到,韩萌觉得她也会把资源放到网上。
她的上一部影片《江南弃儿》,如果能获得主人公的授权,合适的时机是可以释放资源出来的。
“当下的纪录片制作发行体系就不算健全,没有正常的生态,扔资源是自救。”
东楠也说她会的。
“最后一步才会考虑放到国内网上。会和各方面的投资人,其他播出机构以及被拍摄者做好沟通,时机对才会放出资源。”
走到最后一步之前,她们会做很多发行尝试。东楠曾把上一部影片《偷》放在vimeo on demand。在这个平台,作者直接发作品出来,观众付费观看。“《偷》在国内的扩散完全是靠盗版传播,资源不可控制地扩散,但因此收获了很多观众。在这种大环境下,盗版有积极的一面。地下有让人激动的地方。只是那个不是自发的,很被动。”
然而在国内,纪录片的观看与发行尚未形成更细分和垂直的市场和产业模式,对于小体量和独立制作的纪录片,无法在一个完整专业的观看链条和盈利方式持续成长。
当纪录片导演们带着作品离开后期机房,就不得不开始另一种征途。
韩萌和东楠都提到,她们在探索新的方式,这条征程“最终都是为了抵达观众。”

《遥望繁星》剧照
只是,这样迫不得已的抵达方式能持续多久?
身为纪录片导演,东楠自己都想不通同行们靠什么吃饭。
独立纪录片工作者,作为一个可谋生的职业,在国内能否真正存在,她是存疑的:“我也许愿意一两个片子不考虑钱,但也许以后再也不想做纪录片了。“
“搞副业也好,家底厚实也好,自己放片子出来也好,都是个人层面的选择。对于纪录片生态,需要高质量的作品,行业力量的呼吁和支持,还有观众培养。”
韩萌期待拓展更多元的放映渠道,除了更多的民间放映,还可以有大学的教研活动、公益组织的研讨。“我们的纪录片才有可能被更多人看到,并被有针对性的研究。”
原标题:《他或许不是最后一个“扔”资源的纪录片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