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海明威谈写作:创作一旦成了你的大毛病,只有死了才能了结
创意写作坊

记者:在实际写作过程中,你喜欢早晨的时间?
海明威:很喜欢。
记者:你能不能谈谈这个过程?你什么时候工作?有没有一张严格的时间表?
海明威:在写书或写故事的时候,我早晨天一亮就动笔。没有人打扰你,早晨凉爽,有时候冷,你开始工作一写就暖和了。你读一遍你写好了的部分,因为你总是在你知道往下写什么的时候停笔,你现在往下写就是了。你写到自己还有活力、知道下面怎样写的时候停笔,想办法熬过一个晚上,第二天再去碰它。比方说,你早晨六点开始写,可以写到中午,或者不到中午就不写了。你停笔的时候,好像是空了,可同时你没有空,你是满的,这种感受好比你同你所爱的人做过爱之后一样。什么事也不会让你不高兴,什么毛病也不会出,什么事也不要紧,只等第二天早晨你再动笔。难就难在你要熬到第二天早晨。
记者:你离开打字机的时候,你能不去思考你关于写作的种种打算吗?
海明威:当然能。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得有训练。这种习惯,我已经练成了。不练不成。
记者:你重读前一天已经写好的部分时进不进行修改?还是等以后整部作品写完之后再修改?
海明威:我每天总是把停笔之前的稿子修改一遍。全文完成之后,自然再改一遍。别人替你打了字之后,你又有机会改正和重写,因为打字稿看得清楚。最后一次改稿是看校样的时候。你得感谢有这么多次不同的修改机会。
记者:你修改的程度是多大呢?
海明威:这就看情况了。《永别了,武器》的结尾,就是最后一页,我改写了三十九次才算满意。
记者:这里有什么技巧问题没有?你感到为难的是什么呢?
海明威:寻找准确的字眼儿。
记者:你重读的时候是不是激起你的“活力”?
海明威:重读的时候正是你得往下写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你能在那儿激起活力来。活力总是有的。
记者:但是,有没有根本没有一点灵感的时候?
海明威:当然有这种时候。但是,你只要在知道下面将发生什么的时候停笔,你就能往下写。只要你能开个头,问题就不大了。
记者:桑顿·怀尔德谈到一些记忆法,可以使作家继续他每天的工作。他说你有一回告诉他,你削尖了二十支铅笔。
海明威:我不记得我一口气用过二十支铅笔。一天用七支二号铅笔就不错了。
记者:你发现最理想的写作地方是哪儿?从你在那里写的作品数量看,安姆波斯·孟多斯旅馆一定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周围的环境对写作没有多少影响吧?
海明威:哈瓦那的安娜波斯·孟多斯旅馆是非常好的地方。这所农庄也是一个极好的地方,或者说以前是极好的地方。不过,我到哪儿都工作得很好。我是说我不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很好地工作。电话和有人来访是破坏写作的事情。
记者:要写得好是不是必须情绪稳定?你跟我说过,你只有在恋爱的时候才写得好。你可以再发挥一下吗?
海明威:好一个问题。不过,我不妨试试得个满分。只要别人不来打扰,随你一个人写去,你在任何时候都能写作。或者,你狠一狠心便能做到。可是,你恋爱的时候肯定写得最好。如果你也是这样,我就不再发挥了。
记者:经济保障呢?对写好作品有害吗?
海明威:如果钱来得太早,而你爱创作又爱享受生活,那么,要抵制这种诱惑可是需要很强的个性。创作一旦成了你的大毛病,给了你最大的愉快,只有死了才能了结。那时候经济有了保障就帮了大忙,免得你担忧。担忧会破坏创作能力。身体坏同忧虑成比例,它产生忧虑,袭击你的潜意识,破坏你的储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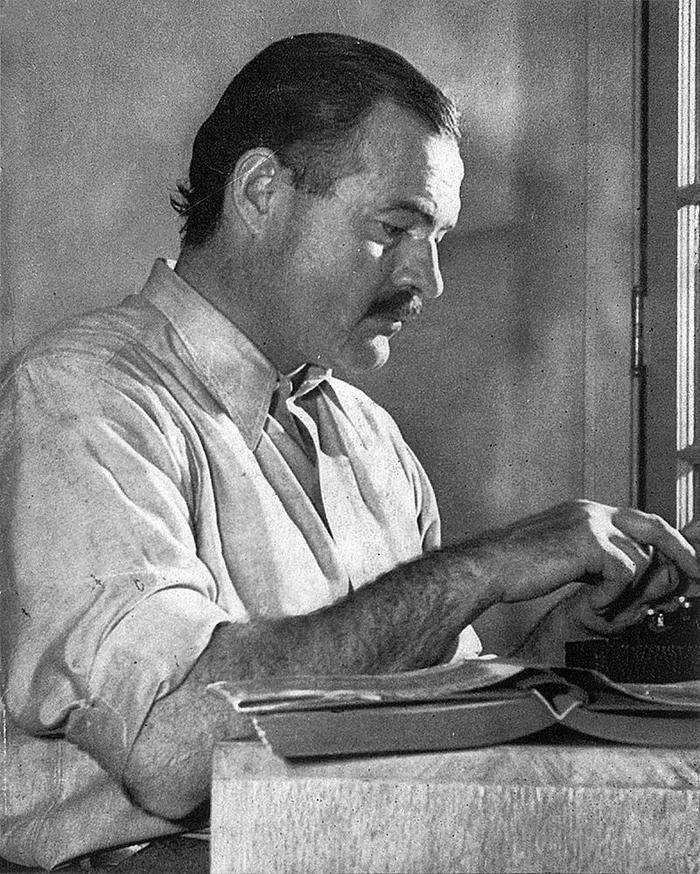
记者:你记得起你想当作家的确切时刻吗?
海明威:不,我一直想当作家。
记者:菲利普·扬在评论你的书里提出,你在一九一八年中了迫击炮弹片、受了重伤,这场震惊对你当作家起了很大的影响。我记得你在马德里简单地提起过他的论著,认为没多大道理,你还说,你认为艺术家的才能不是后天获得的特征,根据门德尔的意思是先天固有的。
海明威:那年在马德里我的脑子显然不算正常。唯一可提的一点是我只是简单地提到扬先生那本书和他关于外伤的文学理论。也许两次脑震荡和那年头盖骨骨折弄得我说话不负责任。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告诉过你,我相信想象可能是种族经验遗传的结果。在得了脑震荡之后愉快、有趣的谈话中,这种说法听来是不错的,不过我以为问题多少正在那里。这个问题等我下一次外伤使我脑子清楚之后再说,现在就谈到这里。你同意吗?我感谢你删去我可能涉及到的亲属的名字。谈话的乐趣在探究,但是许多东西以及一切不负责任的说法都不该写下来。一写下来,你就得负责。你说的时候也许是看看你信不信。关于你提那个问题,创伤的影响是十分不同的。没有引起骨折的轻伤不要紧,有时候还给你信心。影响到骨头,破坏神经的创伤对于作家是不利的,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利的。
记者:对于想当作家的人来说,你认为最好的智力训练是什么?
海明威:我说,他应该走出去上吊,因为他发现要写得好真是难上加难。然后,他应该毫不留情大量删减,在他的余生中尽力写好。至少他可以从上吊的故事写起。
记者:你对于进入学术界的人有什么想法?大量作家到大学去教书,你是不是认为他们牺牲了文学事业,作了妥协?
海明威:这要看你所谓的妥协是什么意思。是受了污损的妇女的用语吗?还是政治家的让步?还是你愿意多付点钱给你的食品店老板或裁缝,可是想晚点付?是这种意义的妥协吗?既能写作又能教书的作家应该两件事都能做到。许多有才能的作家证明他们能做到。我知道我做不到。不过我认为,教书生涯会中止与外界接触的经验,这就可能限制你对世界的了解。然而,了解越多,作家的责任越大,写起来也越难。想写出具有永恒价值的作品是一件全任性的工作,虽然实际写起来一天只有几个小时。作家好比一口井,有多少种井,就有多少种作家。关键是井里的水要好,最好是汲出的水有定量,不要一下子抽光,再等它渗满。我看我是离题了,不过这个问题没意思。
记者:你说年轻作家做做新闻工作好不好?你在《堪萨斯市星报》受到的训练对创作有没有帮助?
海明威:在《星报》工作的时候,你不得不练习去写简单的陈述句。这对任何人都有用。做报馆工作对年轻作家没有坏处,如果及时跳出,还有好处。这是最无聊的老生常谈,我感到抱歉。但是,你既然问别人陈旧的问题,也容易得到陈旧的回答。
记者:你在《大西洋两岸评论》上写道:写新闻报道的唯一好处是收入多。你说,“你写报道,是毁了你有价值的东西,你这是为了赚大钱。”你觉得写这类东西是自我毁灭吗?
海明威:我不记得我这么写过。但是,这话听起来是够愚蠢、够粗暴的了,好像我是为了避免当场说谎才发表这一通明智的谈话似的。我当然并不认为写这类东西是自我毁灭,不过,写新闻报道过了一定的程度对于一位严肃的创作家来说可能是一种日常的自我毁灭。

记者:你觉得同其他作家相处对促进智力有没有价值?
海明威:当然有价值。
记者:你在写作的时候,感没感觉到自己受正在阅读的书籍的影响?
海明威:自从乔伊斯写《尤里西斯》之后,没有感觉到这种影响。他的影响也不是直接的。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了解的那些字不许用,我们不得不为了一个单字而斗争,他作品的影响在于他把一切都变了,我们有可能摆脱限制。
记者:你能从作家身上学到关于写作的东西吗?例如,你昨天对我说,乔伊斯不能容忍谈写作。
海明威:你同本行的人在一起,通常谈论其他作家的作品。自己写了什么,谈得越少,这些作家就越好。乔伊斯是一位非常大的作家,他在写什么,他只跟愚笨的人作些解释。他所尊重的那些作家读了他的作品就能知道他在干什么。
记者:你最近好像避免同作家们在一起。为什么?
海明威:这个问题复杂些。你创作越深入,你越会孤独。你的好朋友、老朋友多数去世了,其他的迁走了。你不常见得着他们,但是你在写,等于同他们有来往,好像过去你们一起呆在咖啡馆里一样。你们之间互通信件,这些信写得滑稽,高兴起来写得猥亵、不负责任,这同交谈差不多。但是你更加孤独,因为你必须工作,而且能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如果浪费时间,你会觉得你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记者:有些人,你的同时代人,对作品的影响怎么样?葛屈露德·斯泰国有没有影响?还有依兹拉·庞德、麦克斯·潘金斯怎么样?
海明威:对不起,我不善于做尸体解剖。对付这些事情,有文学界和非文学界的验尸官。斯泰因小姐关于她对我的影响,写得相当长而且相当不精确。她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她从一部名叫《太阳照常升起》的书里学到了写对话。我很喜欢她,而且认为她学到了如何写对话是件好事。在我看来,尽量向每个人学习,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这并不新鲜,但是对她影响这么强烈,我是没有想到的。她在其它方面已经写得很好了。依兹拉对于自己真正了解的课题是非常精通的。这类谈话,你听了感到厌烦吗?在这个私下谈话中去揭三十五年前的隐私,我很讨厌。这同你说出事情的全貌是不同的。那还有点价值。这里,说简单点为好:我感谢斯泰因,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字与字之间的抽象联系,看我多喜欢她;我重申我对依兹拉作为大诗人和好朋友的忠诚;我非常关心麦克斯·潘金斯,我一直无法相信他是死了。我写的东西,潘金斯从来没叫我改过,除了去掉一些当时不能发表的字眼。去掉的地方留下空白,知道这些字眼的人明白空白的地方该是哪些字。对于我来说,他不是一个编辑。他是一位明智的朋友,极好的同伴。我喜欢他那种戴帽子的方式和嘴唇抽动那种奇怪的样子。
记者:你说谁是你的文学前辈——你学到的东西最多的那些人?
海明威:马克·吐温、福楼拜、司汤达、巴哈、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安德鲁·马韦尔、约翰·多恩、莫泊桑、吉卜林的好作品、梭罗、马利埃特船长、莎士比亚、莫扎特、吉瓦多、但丁、维吉尔、丁都莱多、希罗尼默斯·包士、布鲁盖尔、帕提尼、戈雅、乔陶、塞尚、梵高、高更、圣·胡安·德·拉·克鲁兹、贡戈拉——全想起来要花一天的时间。这样一来,好像我是要卖弄我所不具备的学问,而不是真的想回忆一切对我的生活和创作发生过影响的人。这倒不是一个陈腐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好,是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凭良心回答。我把画家放在里面,或者说开始这么做,是因为我从画家身上学习写作与从作家身上学习写作同样多。你要问这是怎么学的?那要另找一天时间同你解释。我认为,一个作家从作曲家身上,从和声学与对应法上学到东西是比较明显的。

记者:你玩过乐器吗?
海明威:玩过大提琴。我母亲让我学了一整年音乐和对应法。她以为我有能力学音乐,哪知我一点才能也没有。我们在室内组织小乐队——有人来拉小提琴,我姐姐拉中音小提琴,母亲弹钢琴。我呢,大提琴,反正拉得世界上没有比我更糟的了。当然,那一年我还出去干别的事。
记者:你列的那些作家重不重读?比如,吐温。
海明威:读吐温的作品,你得隔两、三年。你记得很清楚。我每年读点莎士比亚,常常是《李尔王》。你读了心里高兴。
记者:这么说来,读书是一种经常性的消遣和乐趣了。
海明威:我总是在读书,有多少读多少。我给自己定量,所以总是有所储备。
记者:我们还是回到你开列的那张名单上去,谈谈一位画家,比如——希罗尼默斯·包士,怎么样?他作品里那种梦魇般的象征好像同你自己的作品相去很远。
海明威:我有过梦魇,所以了解别人的梦魇。但是你不一定把它们写下来。凡是你省略掉你所了解的东西,它们在作品中依然存在,它们的特质会显示起来。如果一个作家省略掉的是他所不了解的东西,它们在作品中就会像漏洞一样显示出来。
记者:这是不是说,你熟悉了你开的名单上那些人的作品之后,你就能灌满你刚才说的那口“井”?还是说,它们会有意识地帮助你提高写作技巧?
海明威:它们是我们学习去看、去听、去想、去感觉或不去感觉以及去写的一个部分。你的“活力”就在那口井里。谁也不知道它是由什么形成的,你自己更不知道。你只知道你是有“活力”呢,还是得等它恢复。
记者:你承不承认你的小说中存在象征主义?
海明威:我想是存在的,因为批评家们不断地找到了象征。对不起,我不喜欢谈象征,也不喜欢别人问。写了书、写了故事,又不被别人要求去解释,真是够难的。这也抢了解释者的工作。如果有五个、六个或者更多的好批评家不断地在解释,我为什么要去干扰他们呢?读我写的书是为了读时的愉快。至于你从中发现了什么,那是你读的时候的理解。
记者:在这个方面继续问一个问题:有一位顾问编辑发现《太阳照常升起》中,在斗牛场登场人物和小说人物性格之间,他感觉到有一点相似。他指出这本书头一句话说罗伯特·柯恩是一个拳击手;后来,在开铁栏时你描写那头公牛用它两只角又挑又戳,活像一个拳击手。那斗公牛见了一头阉牛便被它吸引住,平息下来,无巧不巧,罗伯特·柯恩听从杰克的话,而杰克是阉割过的,正像一头阉牛。迈克一再挑逗柯恩,那位编辑便把迈克看成斗牛士。编辑的论点这样开展下去,但是他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意用斗争仪式的悲剧性结构来框架小说。
海明威:从这些话听来,那位顾问编辑好像有点钻牛角尖。谁说过杰克是“阉割过的,正像一头阉牛”?他是在很不相通的情况下受的伤,他的隐处是完好的,没有受到损伤。因此,作为一个男子的正常感觉,他都具备,可是就是无法过性生活。他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伤在肉体,而不在心理,所以他不是阉割。
记者:这些追究技巧的问题确实叫人恼火。
海明威:明智的问题既不叫你愉快,也不叫你恼火。不过,我仍然认为作家谈论自己如何写作是非常不好的事情。他写作是为了读者用眼睛看,作者去解释或者论说都是不必要的。你可以肯定,多读几遍比初读一遍所得到的东西要多得多,这一点做到之后,叫作者去解释或者叫他在他作品更艰难的国土上去当导游,就不是作者的事情了。
记者:同这一点有关,我记得你也曾经告诫过,说作家谈论自己正在写作过程中的作品是危险的,可以说会“谈没了”。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有许多作家——我想起吐温、王尔德、瑟伯、史蒂文斯——都先把他们写的东西请听众检验,然后修改润色。
海明威:我不相信吐温拿《哈克贝利·芬》给听众“检验”过。如果他这么做,说不定他们让删掉好的东西,加进坏的东西。了解王尔德的人说他讲得比写得好。史蒂文斯也是讲得比写得好。他不论写作还是说话,有时候叫人难以相信,我听说他年纪大了之后许多故事都变了。如果瑟伯谈得跟他写得一样好,他准是一个最了不起、最不叫人生厌的说故事人。我所认识的人中,谈自己行业谈得最好的是斗牛士胡安·贝尔蒙特,他的谈话最令人愉快,也最邪恶。
记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经过多少精心的努力才形成你特殊的风格?
海明威:那是长久以来一个令人生厌的问题,如果你花上两天的时间回答这个问题,你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弄得无法写作了。我可以说,业余爱好者所谓的风格就是不可避免的别扭,那来自你首次尝试去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新的名著几乎没有一部与以前的名著相同。一开始,人们只见到别扭。后来不大看得出来了。当它们显得那么别扭的时候,人们以为这别扭就是风格,于是许多人去模仿。这是令人遗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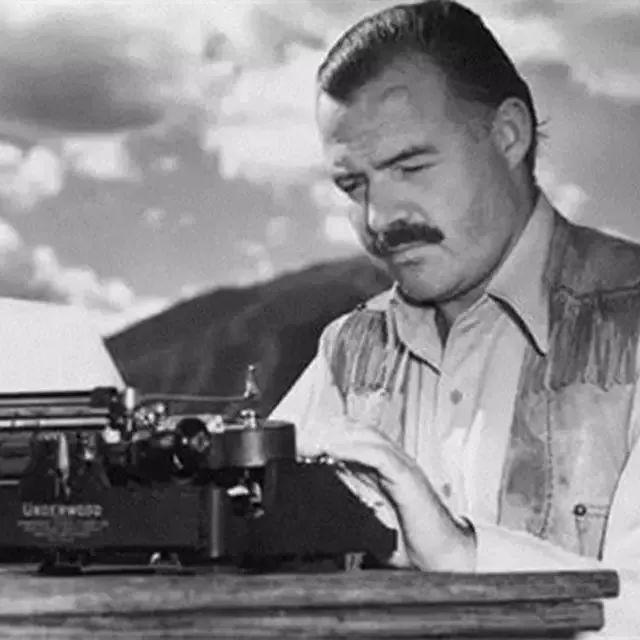
记者:你有一次在信中告诉我,在简陋的环境中能写成各种不同的小说,这种环境对作家是有益的。你能用这一点说明《杀人者》——你说过,这篇小说、《十个印第安人》和《今天是星期五》是在一天之内写成的——或许还有你头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吗?
海明威:我想一想。《太阳照常升起》,我是在我生日那一天,七月二十一日动笔的。我妻子哈德莱和我一早去买看斗牛的票,那是七月二十四日开始的盛会。和我年龄相同的人个个写过一部小说,可我写一段还觉得挺困难。所以我在生日那一天开始写,整个节日都在写,早上在床上写,到马德里又写。那里没有节日盛会,我们订了一间有桌子的房间,我就舒舒服服地伏在桌子上写,旅馆拐角在阿尔凡瑞兹街上有一处喝啤酒的地方,那地方凉快,我也去那儿写。最后热得写不下去,我们就到汉达依去。在那片又大又长的美丽的沙滩上,有一家便宜的小旅馆,我在那儿写得很好,后来又到巴黎去,在圣母院路一一三号一家锯木厂的楼上公寓里写完初稿。从动笔那一天开始,一共写了六个星期。我把初稿拿给小说家纳桑·艾奇看,他那时说话口音很重,他说,“海姆,你说你写了一部小说是什么意思?哈,一部小说。海姆,你是在坐旅游车吧。”我听了纳桑的话并不太灰心,改写了这部小说,保留伏拉尔勃的什伦斯村陶柏旅馆的旅途那部分(关于旅行钓鱼和潘普洛纳那部分)。你提到一天之内写的几篇小说,那是五月十六日在马德里圣·依西德路斗牛场写的。当时外面正下着雪。头一篇我写的是《杀人者》,这篇小说我以前写过但失败了。午餐以后,我上床暖和身子,写了《今天是星期五》。那时候,我活力旺盛,我想我都快疯了,我还有六篇小说要写。因此,我穿上衣服,走到佛尔诺斯那家老斗牛士咖啡馆去喝咖啡,接着回来写《十个印第安人》。这使得我很不好受,我喝了点白兰地就睡了。我忘了吃饭,有一个侍者给送来了一点鳕鱼、一小块牛排、炸土豆,还有一瓶巴耳德佩尼亚斯酒。开膳宿公寓的女主人总担心我吃不饱,所以派侍者来。我记得我当时正坐在床上边吃边喝巴耳德佩尼亚斯酒。那位侍者说他还要拿一瓶酒来,他说女主人问我是不是要写一整夜。我说,不是,我想休息一下。侍者问,你为什么不再写一篇。我说我只想写一篇。他说,胡说,你能写六篇。我说我明天试一试。他说你今天晚上就写。你知道这老太婆干什么给你送吃的来?我说,我累啦。胡说,他说(他没用“胡说”这个词)。你写三篇蹩脚小说就累啦。你翻译一篇我听听。你由我去吧,我说。你不走我怎么写呢?所以我坐了起来喝巴耳德佩尼亚斯酒,心想我头一篇小说如果写得如我期望的那么好,我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作家。
记者:你写短篇小说的时候脑子里构思完整到什么程度?主题、情节或者人物在写的过程中变不变化?
海明威:有时候你知道故事是什么样的。有时候你边写边虚构,不知道最后写成什么样子。一切事物都在运动过程中变化,运动的变化产生故事。有时候,动得这么慢它好像不在动了。但总是有变化、有运动的。
记者:写长篇小说是不是也如此?还是你先有一个总的计划,然后严格遵守?
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是我每天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大体上知道下面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每天写的时候我虚构出小说中所发生的事情。
记者:《非洲的青山》、《有的和没有的》和《过河入林》是不是都是从短篇小说发展成长篇小说的?如果是的,那么这两种体裁非常相似,作家不必完全改变写法就能从一种体裁过渡到另一种体裁,是这样吗?
海明威:不,不是这样。《非洲的青山》不是一部小说,写这部书的意图是想出一部极为真实的著作,看看如果真实地表现一个国土和一个月的活动,能不能与一部虚构的作品相比。我完成《非洲的青山》之后又写了《乞力马扎罗的雪》和《弗兰西斯·麦考伯短暂的幸福生活》这两个短篇。这些故事是我根据那次长时间游猎得到的知识和经验虚构出来的,那次游猎中有一个月的经历,我想把它写成忠实的记实,那便是《非洲的青山》。《有的和没有的》和《过河入林》这两部小说开始时都是作为短篇写的。
记者:你觉得从一种创作计划转变为另一种创作计划是容易的吗?还是你坚持去完成你所开始的写作计划?
海明威:我中断严肃的工作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件事说明我多么愚蠢,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我会受到惩罚的。你别担心。
记者:你想到自己是和别的作家在比高低吗?
海明威:从来没有想过。我过去是想超过一些我认为确有价值的死去的作家。现在,长期以来我只想尽我的努力写好。有时候我运气好,写得超过我能达到的水平。
记者:你认为作家年龄大了以后写作能力会不会衰退?你在《非洲的青山》中提到,美国作家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变成赫巴德老妈妈。
海明威:那个情况我不了解。明白自己要干什么的人只要他们头脑好使就能坚持干下去。在你提到的那本书里,如果你查看一下,你就知道,我是同一个没有幽默感的奥地利人在吹嘘美国文学,我当时要做别的事,他非要我谈。我把当时谈话的内容忠实地记了下来。不是想发表不朽的声明。有相当一部分的看法是不错的。
记者:我们还没有讨论过人物性格。你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是不是毫无例外都取自现实生活?
海明威:当然不是。有的取自现实生活。多数是根据对人的知识和了解的经验之中虚构出来的。
记者:你能不能谈一谈把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变成虚构人物这个过程呢?
海明威:如果我说明我有时是怎么变的,那么这就可以给诽谤罪律师当手册了。
记者:你是不是也象 E·M·福斯特一样,把“平面”人物与“立体”人物区别开来?
海明威:如果你是去描写一个人,那就是平面的,好比一张照片,在我看来这就是失败。如果你根据你所了解的经验去塑造,那他该是立体的了。
记者:你塑造的人物性格中,回想起来感到特别喜爱的是谁?
海明威:这名单开起来就太长了。
记者:那么,你重读你自己作品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要作些修改吗?
海明威:有时候我感到难写下去的时候,我读读自己的作品让自己高兴高兴,于是我想到写作总是困难的,有时候几乎是办不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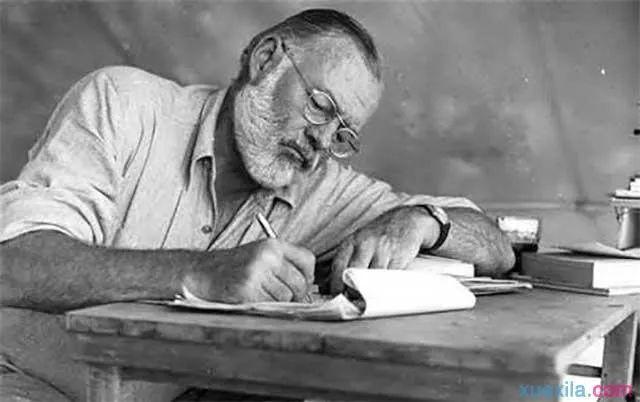
记者:你怎么给你的人物取名字?
海明威:尽我力量取好。
记者:你在写故事的过程中,书名就想好了吗?
海明威:不是的。我写完一篇故事或者一本书之后开列一大串篇名或者书名——有时候多到一百个。然后开始划掉,有时划得一个也不剩。
记者:你有的篇名取自小说原文,例如《白象似的山峰》,也是这样情况吗?
海明威:是的。题名是后来想的。我在普鲁尼尔遇见一位姑娘,我是在吃中饭之前到那儿吃牡蛎去的。我知道她已经打过一次胎。我走了过去,同她聊天,不是聊打胎这件事,但是在回去的路上我想到这篇故事,连午餐都没有吃,花了一个下午时间把它赶了出来。
记者:这么说,你不在写作的时候,也经常在观察,搜求可能有用的东西。
海明威:那当然。作家不去观察,就完蛋了。但是他不必有意识地去观察,也不必去考虑将来如何使用。也许开始的时候是这种情况。但到了后来,他观察到的东西进入了他所知、所见的大仓库。你知道这一点也许有用:我总是试图根据冰山的原理去写作。冰山露出水面的每一部分,八分之七是藏在水面之下的。你删去你所了解的任何东西,这只会加厚你的冰山。那是不露出水面的部分。《老人与海》本来可以长达一千多页,把村里每个人都写进去,包括他们如何谋生、怎么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等。其他作家这么写了,写得很出色很好。在写作中,你受制于他人已经取得的、令人满意的成就。所以我想学着另辟途径。第一,我试图把一切不必要向读者传达的东西删去,这样他或她读了什么之后,就会成为他或她的经验的一部分,好像确实发生过似的。这件事做起来很难,我一直十分努力在做。反正,姑且不谈怎么做到的,我这一次运气好得令人难以相信,能够完全把经验传达出来,并且使它成为没有人传达过的经验。运气好就好在我有一个好老头儿和一个好孩子,近年来作家们已经忘记还有这种事情。还有,大海也同人一样值得写。这是我运气好。我见过马林鱼的配偶,了解那个情况。所以我没有写。就在那一片水面上我看见过五十多头抹香鲸的鲸群,有一次我叉住了一头鲸鱼,这头鲸鱼几乎有六十英尺长,却让它逃走了。所以,我也没有写进小说里去。渔村里我所了解的一切,我都略去不写。但我所了解的东西正是冰山在水面以下的部分。
记者:阿契巴尔德·麦克里什说起过,有一种向读者传达经验的方法,他说是你过去在《堪萨斯市星报》写棒球赛时形成的。这很简单,就用你保存在内心的细节去传达经验,使读者意识到只有在下意识才有所感觉的东西,这样便能达到点明整体的效果……
海明威:这个奇闻不可靠。我从来没有给堪萨斯《星报》写过关于棒球赛的报道。阿契要回忆的是我一九二0年前后在芝加哥怎样努力学习,怎样探求使人产生情绪而又不被人注意的东西,例如一位棒球外野手扔掉手套而不回头看一看手套落在哪里的那副样子,一位拳击手的平底运动鞋在场上发出吱吱扎扎的声音,杰克·勃拉克本刚从监狱出来时发灰的肤色等等,我像画家一样加以素描。你见过勃拉克本那种奇怪的脸色,剃刀刮破的老伤疤,对不了解他历史的人说谎话的方式。这些事情使你激动,写故事是以后的事。
记者:不是亲自了解的情形,你描写过没有?
海明威:那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所谓亲自了解,你是指性欲方面的了解?如果指的是那个,回答是肯定的。一个优秀作家是不会去描写的。他进行创造,或者根据他亲身了解和非亲身了解的经验进行虚构,有时候他似乎具备无法解释的知识,这可能来自已经忘却的种族或家庭的经验。谁去教会信鸽那样飞的?一头斗牛的勇气从何而来?一条猎狗的嗅觉又从何而来?我那次在马德里谈话时头脑靠不住,现在我这是对那次谈话内容的阐述,或者说是压缩。
记者:你觉得对一种经验应该超脱到什么程度才能用小说形式去表现?比如说,你在非洲遇到的飞机碰撞事件?
海明威:这要看什么经验了。有一部分经验,你从一开始就抱完全超脱的态度。另一部分经验就非常复杂。作家应当隔多久才能去表现,我想这没有什么规定。这要看他个人适应调整到什么程度,要看他或她的复原能力。对于一位训练有素的作家来说,飞机着火、碰撞当然是一次宝贵的经验。他很快学到一些重要的东西。至于对他有没有用,决定于他能不能生存下来。生存,荣誉的生存,那个过时而又万分重要的词儿,对于作家来说始终是又困难又重要。活不下来的人常常更为人喜爱,因为人们看不见他们进行长期的、沉闷的、无情的、既不宽恕别人也不求别人宽恕的拼搏,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在死以前应该完成某件任务。那些死得(或离去)较早、较安逸的人们有一切理由惹人喜爱,是因为他们能为人们所理解,富于人性。失败和伪装巧妙的胆怯更富于人性,更为人所爱。

记者:我能不能问一下:你认为作家关心他时代的社会政治问题应该限于什么程度?
海明威:人人都有自己的良心,良心起作用该到什么程度,不应当有什么规定。对于一位关心政治的作家,你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如果他的作品要经久,你在读他作品的时候得把其中的政治部分跳过去。许多所谓参予政治的作家们经常改变他们的政治观点。这对于他们,对于他们的政治——文学评论,很富于刺激性。有时候他们甚至不得不改写他们的政治观点……而且是匆匆忙忙地改写。也许作为一种追求快乐的形式,这也值得尊重吧。
记者:依兹拉·庞德对种族隔离主义者卡斯帕发生了影响,这是不是也影响了你,你还认为那位诗人应该从圣·伊丽莎白医院释放出来吗?
海明威:不。没有一点影响。我认为依兹拉应该释放,应该允许他在意大利写诗,条件是他保证今后不再参预任何政治。我能看到卡斯帕尽快入狱就很高兴。大诗人未必当女生向导,未必当童子军教练,也不一定要对青年发生极好的影响。举几个例子,魏尔伦、兰波、雪莱、拜伦、波德莱尔、普鲁斯特、纪德等人,不该禁闭起来,只是因为害怕他们的思想、举止或者道德方面为当地的卡斯帕所模仿。
记者:你能说你的作品里没有说教的意向吗?
海明威:说教是一个误用的词,而且用糟了。《午后之死》是一本有教益的书。
记者:听说一个作家在他通篇作品中只贯穿一个或两个思想。你说你的作品反映一种或两种思想吗?
海明威:这是谁说的。这话太简单了。说这话的人自己可能只有一种或两种思想。
记者:好,也许这样说更好一些:格拉姆·格林说过,一书架小说由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感情所支配,形成一种统一的系列。我相信,你自己也说过,伟大的创作出自对于不正义的感觉。一位小说家就是这样——被某种紧迫的感觉所支配,你认为这是重要的吗?
海明威:格林先生发表声明的才能,我并不具备。在我看来,不可能对一书架小说、一群鹬鸟或者对一群鹅作一个概括。不过,我还是想概括一下。一个对正义与非正义没有感觉的作家还不如为特殊学生去编学校年鉴,可以多赚点钱。再概括一条。你看,一目了然的事情是不那么难概括的。一位优秀的作家最主要的才能在于他是一位天生的、不怕震惊的检察谎言的人。这是作家的雷达,一切大作家都具备。
记者:最后,我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你作为一位创作家,你认为你创作的艺术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表现事实而不写事实本身?
海明威:为什么为那种事费脑筋?你根据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根据现存的事情,根据你知道和你不可能知道的一切事情,你根据这一切进行虚构,你创造出来的东西就不是表现,而是一种崭新的东西,它比实际存在的真实的东西更为真实,你把它写活了,如果写得好,它就够不朽。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写作,而不是因为你所意识到的别的原因。可是,一切没有人意识到的原因又怎么样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