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巴芮
编辑 | 张薇
视频编导 | 吕方
还是一个音乐人,只是不动手沈黎晖是一个能够迅速抓住事情本质的人。所以对于那种只能为独立音乐带来短期流量爆发的传播方式,他从不看重。无论是在他耳边躁了一夏的《乐队的夏天》,还是两年前将嘻哈搬上主流台面的《中国有嘻哈》,别人再怎么说他是幕后赢家,这位摩登天空——国内最大规模新音乐独立唱片公司的老板也只是付之一笑。10月30日摩登天空Music Plus发布会上,一袭黑衣的沈黎晖站在巨大发亮的屏幕前,标志的披头士发型从他玩儿上乐队那天起就再未改变,只不过在一个已经51岁的男士头上多出一丝慵懒,宽大的黑框眼镜将一张透着年少反叛精神却又被成熟企业家强行压制住的脸遮去一半。“从综艺来讲,今年是原创音乐大年”,沈黎晖说,“但不是综艺改变了我们,是我们改变了综艺”,他向台下俯首一笑,“今天牟頔也来了。”牟頔是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出品方米未传媒的COO。“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就是融合,综艺就是融合发展的一种表现”,沈黎晖接了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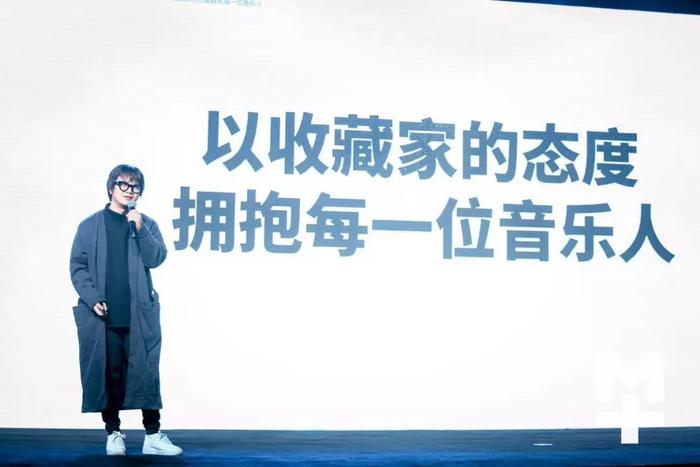 两年前,摩登天空旗下嘻哈厂牌M_DSK派出的5名歌手占据了《中国有嘻哈》前9名中占了1/3,包括并列冠军的PG One。嘻哈从地下升至台面,随着PG One所在的嘻哈团体红花会声名大噪,不久后便闹着与摩登天空解了约。在被乐队躁起来的2019年夏天,这个团体彻底解散了。名利的骤然降临轰掉了心智未稳的嘻哈少年前程。沈黎晖一点不觉得意外,人性嘛,做成第一场音乐节的时候整个公司都跟着他膨胀,好像没有自己干不了的事儿。只不过,红花会的生活变换太快,膨胀速度不是一个量级。又是一届音乐综艺季,参与《乐队的夏天》录制的31支乐队中,5支出自摩登天空,最终还包揽了冠亚军。出于前车之鉴,摩登天空的公关团队甚至早就做下了应对舆情的准备,但这次并没有什么意外发生,也没有人提出奇怪的合作要求——作为出道20年以上的音乐节压轴老牌乐队,这种备受追捧的场面新裤子和痛仰早就见怪不怪了。节目播出期间沈黎晖一直没看,但他知道新裤子得了冠军,之后的某次碰面中提到《乐队的夏天》,沈黎晖问新裤子主唱彭磊,“膨胀了吗?”对方答没有,一副看穿小心思的狡黠模样从沈黎晖上翘的嘴角和目光中流露出来,“我觉得不可能不膨胀”,胜利与被认可终究会将人的自我感知撑大一点。媒体专访、杂志封面、广告片的邀约接踵而来,在这个夏天,新裤子成员们穿着不同的裤子摆出不同的Pose出现在大众媒体的各个位置,直到消耗掉最后一丝暑热,才随着秋凉平静下来。沈黎晖看不上这些,“都是仨瓜俩枣,他们拍那破广告能给几个钱”,实话没做任何伪装就溜出了口,这位新裤子的老板赶忙找补了一句,“这话可能要剪掉”。因一时热度接几个广告或者短暂受到媒体追捧,都不是沈黎晖的追求,短期效益挣些快钱无可厚非,但对长期价值而言,没什么用。而检验流量的唯一标准是票房,“拿钱投票,这个是做不了假的,这个事比什么都重要”,沈黎晖觉得这才是衡量艺术家(摩登天空将签约艺人统一称为艺术家)价值的最直观与最核心的,其他只能算是附加值。但这一标准是在2007年后才生效的,因为在那之前乐队很少能从国内的音乐节主办方得到酬劳。当综艺带来的流量泡沫被时间冲散后,依然能够产生这些价值的,就只有真正好的音乐与内容。沈黎晖愿意为优质内容买单,好比他曾为在音乐节上请来被称作电音摇滚传奇的神童乐队(the Prodigy),对方提了200页包括一套单独声音系统在内的演出需求他悉数满足一样。2018年初,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顶级数控模拟调音台AMS NEVE 88RS首次登录中国,被放进了摩登天空的录音棚。“哇!NEVE调音台,开什么玩笑啊,都是那种最经典最大的乐队才会用到。”摩登天空签约乐队重塑雕像的权利主唱华东记得,那个耗资2000万的录音棚还没建好时,沈黎晖就把他们都叫了去,指着一个空台面说,“NEVE调音台就放在这,下次你们可以在这儿录。”沈黎晖的那份开心让华东想起小时候攒好多钱终于得到了一个擎天柱的感觉。
两年前,摩登天空旗下嘻哈厂牌M_DSK派出的5名歌手占据了《中国有嘻哈》前9名中占了1/3,包括并列冠军的PG One。嘻哈从地下升至台面,随着PG One所在的嘻哈团体红花会声名大噪,不久后便闹着与摩登天空解了约。在被乐队躁起来的2019年夏天,这个团体彻底解散了。名利的骤然降临轰掉了心智未稳的嘻哈少年前程。沈黎晖一点不觉得意外,人性嘛,做成第一场音乐节的时候整个公司都跟着他膨胀,好像没有自己干不了的事儿。只不过,红花会的生活变换太快,膨胀速度不是一个量级。又是一届音乐综艺季,参与《乐队的夏天》录制的31支乐队中,5支出自摩登天空,最终还包揽了冠亚军。出于前车之鉴,摩登天空的公关团队甚至早就做下了应对舆情的准备,但这次并没有什么意外发生,也没有人提出奇怪的合作要求——作为出道20年以上的音乐节压轴老牌乐队,这种备受追捧的场面新裤子和痛仰早就见怪不怪了。节目播出期间沈黎晖一直没看,但他知道新裤子得了冠军,之后的某次碰面中提到《乐队的夏天》,沈黎晖问新裤子主唱彭磊,“膨胀了吗?”对方答没有,一副看穿小心思的狡黠模样从沈黎晖上翘的嘴角和目光中流露出来,“我觉得不可能不膨胀”,胜利与被认可终究会将人的自我感知撑大一点。媒体专访、杂志封面、广告片的邀约接踵而来,在这个夏天,新裤子成员们穿着不同的裤子摆出不同的Pose出现在大众媒体的各个位置,直到消耗掉最后一丝暑热,才随着秋凉平静下来。沈黎晖看不上这些,“都是仨瓜俩枣,他们拍那破广告能给几个钱”,实话没做任何伪装就溜出了口,这位新裤子的老板赶忙找补了一句,“这话可能要剪掉”。因一时热度接几个广告或者短暂受到媒体追捧,都不是沈黎晖的追求,短期效益挣些快钱无可厚非,但对长期价值而言,没什么用。而检验流量的唯一标准是票房,“拿钱投票,这个是做不了假的,这个事比什么都重要”,沈黎晖觉得这才是衡量艺术家(摩登天空将签约艺人统一称为艺术家)价值的最直观与最核心的,其他只能算是附加值。但这一标准是在2007年后才生效的,因为在那之前乐队很少能从国内的音乐节主办方得到酬劳。当综艺带来的流量泡沫被时间冲散后,依然能够产生这些价值的,就只有真正好的音乐与内容。沈黎晖愿意为优质内容买单,好比他曾为在音乐节上请来被称作电音摇滚传奇的神童乐队(the Prodigy),对方提了200页包括一套单独声音系统在内的演出需求他悉数满足一样。2018年初,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顶级数控模拟调音台AMS NEVE 88RS首次登录中国,被放进了摩登天空的录音棚。“哇!NEVE调音台,开什么玩笑啊,都是那种最经典最大的乐队才会用到。”摩登天空签约乐队重塑雕像的权利主唱华东记得,那个耗资2000万的录音棚还没建好时,沈黎晖就把他们都叫了去,指着一个空台面说,“NEVE调音台就放在这,下次你们可以在这儿录。”沈黎晖的那份开心让华东想起小时候攒好多钱终于得到了一个擎天柱的感觉。 请神童乐队是为了向行业内的人证明音乐节的规模和高度,做一些“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花大钱买顶级调音台是为了巩固唱片工业最核心的部分。自12年前出完清醒乐队的第二张专辑《明日的荣耀》后,沈黎晖作为乐队主唱的身份便结束了,外界对他的评价从“一个开公司的乐队主唱”变成“一个玩儿乐队的商人”,但在清醒乐队鼓手郭一环眼中,沈黎晖还是一个音乐人,“只是不动手”,他在用一套特有的商业模式玩儿音乐。
请神童乐队是为了向行业内的人证明音乐节的规模和高度,做一些“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花大钱买顶级调音台是为了巩固唱片工业最核心的部分。自12年前出完清醒乐队的第二张专辑《明日的荣耀》后,沈黎晖作为乐队主唱的身份便结束了,外界对他的评价从“一个开公司的乐队主唱”变成“一个玩儿乐队的商人”,但在清醒乐队鼓手郭一环眼中,沈黎晖还是一个音乐人,“只是不动手”,他在用一套特有的商业模式玩儿音乐。赚钱就是为了玩音乐
刚开始写歌的时候,沈黎晖连吉他和弦都还没弹明白。凭直觉,哪个音按出来好听就哪个 ,所以清醒乐队早期的歌曲中会出现很多奇怪的和弦。这种状况一直到1994年科班出身的鼓手郭一环加入才得以缓解。但沈黎晖不在乎,没有规则的约束与技法加工,反而能将心底最为原始的感受表达清楚。乐队组建于1988年,那年沈黎晖20岁,在北京市工艺美校读三年级。从小就想当明星的那股欲望将他推进校园中最能出风头的圈子,比如全是高年级学生的足球队,在黑灯舞会上跳霹雳舞的时髦青年,以及,一个玩儿摇滚的乐队。将这些行为放至青春期男性身上,能帮助他们高效达成一个最为直接的目标——泡妞儿。激起沈黎晖组乐队欲望的,是留着八十年代新浪潮标志性大长头发的的几个男青年,他们穿着同样新潮的大长袍子在学校里排练Sting的歌,沈黎晖觉得这太帅了。他组队的标准不是技法娴熟,而是要长得帅。于是他相中了服装专业的于凯,“我说你会弹吉他吗?他说不会,但我想弹。我说好,那咱俩就组个乐队吧。”于凯同班的一个大高个儿找到沈黎晖想要加入乐队,“我说你会打鼓吗?不会,我说学吧。”那会儿的沈黎晖也只是自己琢磨着弹一点吉他。虽然父亲是上个年代著名的作曲家,自己也是音协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但沈黎晖从未接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技术“都不怎么样”的几个人组成的乐队叫π,水平差得扒不下任何一首成熟乐队的歌,沈黎晖只能自己写,用最简单的旋律。当时沈黎晖给自己制定的人生目标是摇滚明星,后来加入的鼓手郭一环与其目标不一致,他想成为大师,打鼓中国第一好,被沈黎晖奚落,“你打一辈子鼓也还是一鼓手,有什么用?”郭一环一想也是,随着清醒成名后便逐渐转为制作人,现任摩登天空音乐监制。 一年后,有了七八首原创歌曲的π乐队在班级教室开了一场演唱会,特别成功。好多人,走廊里都是踩着不知从哪儿搬来的桌子的人,抻着脖子透过高墙上的玻璃窗往里张望。沈黎晖挤出人群去换上了他准备好的演出服——一条破洞牛仔裤,又从人群里挤回来。太兴奋了,第一首歌就唱错了调,“重来一遍”,沈黎晖喊。几首歌过后,演出结束,黑板上的字被人群蹭的一干二净,于凯跑回家跟他妈说,“我们成功了!”沈黎晖觉得那就是他玩乐队的顶点,再往后都不算——出专辑斩获各项大奖不算,成为电台收听率最高的乐队不算,登上万人瞩目的舞台也不算,“那种兴奋是没办法替代的,就是那第一次被认可的那种感觉”,沈黎晖说。他们成了学校里的明星,女孩们爱慕的小纸条被接连不断地递到他们手中。这是沈黎晖脑海中最完整的一块记忆,开了头便可以被年少时的激昂推着一股脑向下,使人情绪饱满。就像他那辆永远第一个出现在公司停车场的黑色奔驰SUV轮下的、通往阿那亚的、顺畅的高速公路。他要去看旗下艺术家海龟先生在那举办的一场与以往形式不同的演出。1991年,π乐队更名为清醒。1990年代,摇滚的黄金盛世,乐队的萧条时期。乐手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演出,但那时既没有live house也没有音乐节 ,他们在各个地下或地上的Party串场,那时面孔的演出最多时一周能有一场,跟老板分票账,收入高的一人一百块钱,而痛仰只有几十块钱。没法指望玩儿音乐养活自己。美校毕业后,沈黎晖被父亲安排进中国录音录像做平面设计,负责封面印刷。从小就精于倒买倒卖的沈黎晖发现这是个挣钱行当,于是找人弄了台印刷机,拉上当时在鼓楼摆烟摊儿的个体户朋友干印刷。“挣钱的买卖”在头三年赔的稀里哗啦,“那机器特次,什么活儿都印不出来”,沈黎晖拆东墙补西墙,最后赔了20多万。在人均月薪不过300块的1993年,沈黎晖觉得自己到了世界末日。“我得背一辈子债,梦想就没法实现,我必须要让我的乐队出唱片”,于是他拿着账上仅剩的几万块钱,找来石头、粉雾、佤族、皇冠和D.D.节奏录了张合辑,就是后来被称为摇滚合辑范本的《摇滚’94》。那时的清醒从未有过录音经验,里面只收录了《石头心》和《需要》两首歌。一定程度上,《摇滚’94》满足了沈黎晖从小对于表达和出版的欲望。那时,做电台、出杂志,包括电视电影和音乐都是被记录在沈黎晖的愿望清单上。唯印刷没有。后来印刷公司走上正轨,沈黎晖到处跑业务,经常穿着西服去排练,胳膊底下还夹着包,一点儿也不摇滚,但这是他和他的乐队继续走下去的必要条件。“我从来没有热爱过印刷行业,我相信没有谁会热爱印刷行业,我的目的是赚钱,赚钱就是为了玩音乐。”到阿那亚的路程还剩百余公里,手把在方向盘上,沈黎晖说,“我信念特别坚定。”
一年后,有了七八首原创歌曲的π乐队在班级教室开了一场演唱会,特别成功。好多人,走廊里都是踩着不知从哪儿搬来的桌子的人,抻着脖子透过高墙上的玻璃窗往里张望。沈黎晖挤出人群去换上了他准备好的演出服——一条破洞牛仔裤,又从人群里挤回来。太兴奋了,第一首歌就唱错了调,“重来一遍”,沈黎晖喊。几首歌过后,演出结束,黑板上的字被人群蹭的一干二净,于凯跑回家跟他妈说,“我们成功了!”沈黎晖觉得那就是他玩乐队的顶点,再往后都不算——出专辑斩获各项大奖不算,成为电台收听率最高的乐队不算,登上万人瞩目的舞台也不算,“那种兴奋是没办法替代的,就是那第一次被认可的那种感觉”,沈黎晖说。他们成了学校里的明星,女孩们爱慕的小纸条被接连不断地递到他们手中。这是沈黎晖脑海中最完整的一块记忆,开了头便可以被年少时的激昂推着一股脑向下,使人情绪饱满。就像他那辆永远第一个出现在公司停车场的黑色奔驰SUV轮下的、通往阿那亚的、顺畅的高速公路。他要去看旗下艺术家海龟先生在那举办的一场与以往形式不同的演出。1991年,π乐队更名为清醒。1990年代,摇滚的黄金盛世,乐队的萧条时期。乐手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演出,但那时既没有live house也没有音乐节 ,他们在各个地下或地上的Party串场,那时面孔的演出最多时一周能有一场,跟老板分票账,收入高的一人一百块钱,而痛仰只有几十块钱。没法指望玩儿音乐养活自己。美校毕业后,沈黎晖被父亲安排进中国录音录像做平面设计,负责封面印刷。从小就精于倒买倒卖的沈黎晖发现这是个挣钱行当,于是找人弄了台印刷机,拉上当时在鼓楼摆烟摊儿的个体户朋友干印刷。“挣钱的买卖”在头三年赔的稀里哗啦,“那机器特次,什么活儿都印不出来”,沈黎晖拆东墙补西墙,最后赔了20多万。在人均月薪不过300块的1993年,沈黎晖觉得自己到了世界末日。“我得背一辈子债,梦想就没法实现,我必须要让我的乐队出唱片”,于是他拿着账上仅剩的几万块钱,找来石头、粉雾、佤族、皇冠和D.D.节奏录了张合辑,就是后来被称为摇滚合辑范本的《摇滚’94》。那时的清醒从未有过录音经验,里面只收录了《石头心》和《需要》两首歌。一定程度上,《摇滚’94》满足了沈黎晖从小对于表达和出版的欲望。那时,做电台、出杂志,包括电视电影和音乐都是被记录在沈黎晖的愿望清单上。唯印刷没有。后来印刷公司走上正轨,沈黎晖到处跑业务,经常穿着西服去排练,胳膊底下还夹着包,一点儿也不摇滚,但这是他和他的乐队继续走下去的必要条件。“我从来没有热爱过印刷行业,我相信没有谁会热爱印刷行业,我的目的是赚钱,赚钱就是为了玩音乐。”到阿那亚的路程还剩百余公里,手把在方向盘上,沈黎晖说,“我信念特别坚定。”从野战到正规军1997年,成立近十年的清醒乐队已经成熟,沈黎晖觉得,出专辑的时候到了。但行业不觉得,它们还低迷着。“当时行业已经非常不景气了,大家都没什么钱。”沈黎晖记得当年为许巍、郑钧等摇滚老炮儿出过唱片的红星生产社给他们的制作预算是10万块。太低了,根本无法实现沈黎晖用胶片拍MV的想法。那时正处于模拟转数字的过渡阶段,大多MV画质不清。沈黎晖觉得“完全不行”。他们的专辑必须好,“这就是一个人做事的基础”,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当时行业到底有多难,“实际上已经没什么产出了。”好在印刷公司早有起色,年营业额已经达到七八百万,沈黎晖也成了彭磊眼中的“阔佬”,于是他准备自己掏钱出唱片。沈黎晖曾在公开演讲中提到,“我为了让自己这个自费歌手好看一点,就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公司,假装自己是个公司签约的乐队。”但公司不能只签一支乐队,于是他又找来了新裤子和超级市场,都是他美校的学弟,“(除了他们)我不认识别的人,别人也不相信我。”一个玩笑般的开场,让圈子里的一些人“觉得有点逗又想乐见其成。”沈黎晖成立的公司叫摩登天空,当时还挂在印刷公司下面。所以新裤子彭磊跟人说自己签了个印刷公司。那会儿摩登天空一共仨人——沈黎晖、郭涛和郭一环。除了沈,另外俩人都对新裤子不满意,“小样儿特糙,音不稳,弦都不准”,郭一环觉得“肯定没戏,出不来。”但沈黎晖坚持,后来郭一环才知道,他的审美不是看音乐技术,“他就听那劲儿,特真、纯,摇滚乐不是就讲究这样嘛。”1997年,清醒乐队第一张专辑《好极了!?》出版,花了70万,可以在当时的北京买好几套房的价钱。封面上的人短发、西装,区别于此前摇滚乐手的长发、夹克。彼时的小学生李帅有一种“错觉”,觉得摩登是全中国最酷的音乐公司,“可有钱了,生活品质非常高,觉得他们都是明星”,他记得清醒的MV上了MTV电视台,“我觉得这些人特别厉害。”现在,他是摩登天空旗下视觉厂牌MVM的主理人。《好极了!?》很快卖出20万张,清醒乐队也成了年度最佳乐队,赢了所有排行榜。 一年后,新裤子发片,也卖了好几十万。沈黎晖不可避免地膨胀了,“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干。”在卡带末期,向着商业进发,办杂志、开Live house、发行自己喜欢的国外乐队的唱片。对于摇滚明星的追求,在专辑发行后就结束了。在那样一个传统年代,看见所有音像店都贴着印有自己脸的唱片海报,沈黎晖却觉得有点儿无聊,“这人谁?跟我好像也没什么关系。”乐队的节奏慢了下来。因为对印刷的痛恨,沈黎晖在运营摩登天空时抛弃了之前所有的商业经验,“我要进入到一个完全创造性的自由的领域”,没有打卡,没有规则。就像最初做乐队的时候,“觉得酷,就一帮人扑上去把这事干了。”比如做杂志时产生一个很有创意的广告,整个团队all in进去一个半月;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了第一届摩登天空音乐节,一群人为一个灯箱折腾两周。李帅感受过那种“混乱”。大概2010年,还在媒体的李帅曾跟摩登天空有过一次合作,但他很难适应这个公司的节奏。“特别集中爆发,一件事一堆人全上,气质特别野战,挺凶挺酷的。”他总是一进门就能看到大吼大叫的人、脱了裤子在桌上蹦的人,以及喊着“我要自由的人”,那让他一进去就大脑一片空白,后来几年都没再接过沈黎晖电话。紧接着,CD时代来临,盗版成本降低,“感觉自己好像还不错的时候,唱片销量就突然下降了,杂志也出现了很多问题”。2000年左右,开张三年的摩登天空亏损300万,沈黎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做法。“我突然意识到,这跟印刷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沈黎晖说。早期做印刷公司的时候,每个月会接十几个订单,这些订单从谈判接单到设计打样,再到加工送货结账,都是他自己。对一个摇滚青年而言,高重复性工作简直是在自我伤害,但后来沈黎晖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训练,这复杂的程序磨练了他的执行力与严谨度,“因为出了差错你就拿不到钱。”这让沈黎晖变得务实,在4年后的彩铃时代,他靠着这种接订单干活的能力让摩登天空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活了下来——为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大企业做音乐相关服务。中间亏损的那四年,沈黎晖卖了北京的四套房勉力维持,但大多时间他都躲在花园桥的地下室里没完没了的写歌录歌,“那段时间我们每投一张唱片都是摩登的最后一张唱片的感觉。”沈黎晖记得有一年年前,他将公司最后的几万块钱给了一名艺术家当制作费,那时还在摩登天空任职的丁太升特别恨那个艺术家,“说你知道吗,你拿的是我们过节的钱”,沈黎晖回忆到。
 抠,也是从那时开始的。“特别难,就是我付你这钱我也知道赚不回来,就得设定各种各样的条件,比如你说这个专辑能不能拍个music video,不能,全是否定的”,沈黎晖说。此后,沈黎晖开始认真对待每一笔预算,比如彭磊在《乐队的夏天》上说他连个弦乐队都不给请。看到那笔预算审批的时候沈黎晖质疑了一下,“这钱难道不应该是节目组出吗?他们说节目组预算就给了两万,我说两万能请什么就请什么吧,你为什么要自己额外拿钱干这事?”沈黎晖说这是一种预算制,“跟我对你好不好没关系,每笔预算必须要有出处。”虽然已经进化,但沈黎晖觉得公司的财务流程还是不够严密,“这些应该到财务那儿就给否掉了,不应该到我这儿。”沈黎晖早已摒弃了最初抓不住重点的艺术家思维,现在这些严密的流程才更重要,“这样才能保证你的生存。”沈黎晖也随之放弃了自我的一部分,是摇滚明星的那部分。当别人说他是一个乐队主唱,言外之意这人根本做不了运营,或者早期自己被乐队当做“提款机”,这些曾经刺痛他的东西现在已经越来越没力量了,“我现在可以接受任何的一个角色。”2016年李帅入职摩登天空时明显的觉出了这家企业的变化,虽然在桌子上蹦的人依然存在,但似乎更有秩序。而现在,摩登天空里喊着要自由的新新人类们,手机里也都装上了钉钉。
抠,也是从那时开始的。“特别难,就是我付你这钱我也知道赚不回来,就得设定各种各样的条件,比如你说这个专辑能不能拍个music video,不能,全是否定的”,沈黎晖说。此后,沈黎晖开始认真对待每一笔预算,比如彭磊在《乐队的夏天》上说他连个弦乐队都不给请。看到那笔预算审批的时候沈黎晖质疑了一下,“这钱难道不应该是节目组出吗?他们说节目组预算就给了两万,我说两万能请什么就请什么吧,你为什么要自己额外拿钱干这事?”沈黎晖说这是一种预算制,“跟我对你好不好没关系,每笔预算必须要有出处。”虽然已经进化,但沈黎晖觉得公司的财务流程还是不够严密,“这些应该到财务那儿就给否掉了,不应该到我这儿。”沈黎晖早已摒弃了最初抓不住重点的艺术家思维,现在这些严密的流程才更重要,“这样才能保证你的生存。”沈黎晖也随之放弃了自我的一部分,是摇滚明星的那部分。当别人说他是一个乐队主唱,言外之意这人根本做不了运营,或者早期自己被乐队当做“提款机”,这些曾经刺痛他的东西现在已经越来越没力量了,“我现在可以接受任何的一个角色。”2016年李帅入职摩登天空时明显的觉出了这家企业的变化,虽然在桌子上蹦的人依然存在,但似乎更有秩序。而现在,摩登天空里喊着要自由的新新人类们,手机里也都装上了钉钉。最擅长的事情是“破坏”但建立制度并不代表摩登天空将走向职业的范式,为了配合企业扩张后的高效运转而已。当下的摩登天空早已不再是那个只有个位数员工的工作室了,200余名工作人员和160多组签约艺术家让它更像一个庞大音乐帝国。“职业化没意思”,毕竟沈黎晖最乐于也最擅长的事情是“破坏”。早期清醒和新裤子出的专辑,从音乐风格到封面设计,每一样都跟同时期的范本不同,新东西就是一种“破坏”。还有向内的自我破坏,比如做摇滚起家的摩登天空在2016年成立M_DSK嘻哈厂牌。“我想说这就是摇滚,摇滚乐是一种音乐,摇滚是让你有破坏和打破的精神。”沈黎晖说,“不管你干什么,不管你用什么形式,我觉得这种能打破能创新的就是摇滚。所以我们追随的是摇滚,而不是摇滚乐。”
 沈黎晖干了一件特别摇滚的事儿——2007年,在公司账面只有一百万的情况下,他要办一场音乐节,据说总共不足十人的员工中就有一名宣传主管当即辞职。沈黎晖是受到了2002年时在瑞典胡尔茨弗雷德市在原始森林内举办的大型摇滚音乐节的感召,他想办这样一场音乐节,像一个大Party,而不是国内流行的“苦大仇深的垃圾筒”。“不管它挣钱不挣钱,我们得告诉大家,音乐节应该长这样。”没人有过这种经验,当年全国一共4个音乐节。被拉来当现场主舞台导演的是郭一环,“我说什么叫现场导演?他说你去打听打听上网查查。他就敢这么干,真横。这是一个我,还有无数个“我”那么多人,就这么干。”郭一环觉得沈黎晖真是胆大。现场无疑是混乱的,乱到沈黎晖直接关了冲着他吼的对讲机,躲在后台一角,一个多小时后,外面一片欢呼音浪。他们成功了。分管商务与市场的摩登天空副总裁沈玥是当时参与举办音乐节的一员,他跟沈黎晖当时都有一种“这事儿肯定能成”的感觉。沈黎晖说回看之前的采访,觉得那时充满了一股牛逼轰轰的感觉,也不知有什么样的资本和勇气说出这话。沈玥记得当时摩登天空音乐节的计划特别庞大,有很多舞台,把场地都占满了,而且每个舞台风格都不一样。“当时就觉得这个有必要做这么大吗?”他看到了沈黎晖的野心与想象力,“用的是迷笛以前的场地,但内容是迷笛的好几倍。”但这些“内容”也将摩登账上的一百多万烧光了。此后国内音乐节遍地开花,高峰期一年两百多个。而摩登天空音乐节和草莓音乐节则是绝对的头部。独音唱片的老板郭诚曾说,“自2007年摩登举办第一届音乐节开始,中国80%的乐队应该感谢沈黎晖。经历过来的乐队应该都清楚,是他让大家有了更客观的收入。”音乐节为独立音乐人创造了输出渠道,完成了音乐工业体系的最后一步,使之成为闭环。更重要的是,沈黎晖明确这是一个商业行为,他按照演出乐队带来的市场价值付费,终结了此前乐队在音乐节上“免费”演出的境况。现在乐队也可以根据市场行情进行议价。那次音乐节颠覆了很多传统——比如让刚出了一张专辑的国内新乐队重塑雕像的权利压轴;摒弃了请国外经典老牌乐队的传统,转而选择了正当红的新乐队Yeah Yeah Yeahs。一切都既大胆又新鲜。如彭磊所言,沈黎晖的世界观就是时髦,“他一直就是要新的,做之前的人没有经验做的事。”2017年摩登天空在英国利物浦开了分公司,甚至将音乐节也输出到了国外。在10月30日的发布会上,沈黎晖说,曾有4组摩登天空的艺术家登上英国独立音乐榜的Top50。
沈黎晖干了一件特别摇滚的事儿——2007年,在公司账面只有一百万的情况下,他要办一场音乐节,据说总共不足十人的员工中就有一名宣传主管当即辞职。沈黎晖是受到了2002年时在瑞典胡尔茨弗雷德市在原始森林内举办的大型摇滚音乐节的感召,他想办这样一场音乐节,像一个大Party,而不是国内流行的“苦大仇深的垃圾筒”。“不管它挣钱不挣钱,我们得告诉大家,音乐节应该长这样。”没人有过这种经验,当年全国一共4个音乐节。被拉来当现场主舞台导演的是郭一环,“我说什么叫现场导演?他说你去打听打听上网查查。他就敢这么干,真横。这是一个我,还有无数个“我”那么多人,就这么干。”郭一环觉得沈黎晖真是胆大。现场无疑是混乱的,乱到沈黎晖直接关了冲着他吼的对讲机,躲在后台一角,一个多小时后,外面一片欢呼音浪。他们成功了。分管商务与市场的摩登天空副总裁沈玥是当时参与举办音乐节的一员,他跟沈黎晖当时都有一种“这事儿肯定能成”的感觉。沈黎晖说回看之前的采访,觉得那时充满了一股牛逼轰轰的感觉,也不知有什么样的资本和勇气说出这话。沈玥记得当时摩登天空音乐节的计划特别庞大,有很多舞台,把场地都占满了,而且每个舞台风格都不一样。“当时就觉得这个有必要做这么大吗?”他看到了沈黎晖的野心与想象力,“用的是迷笛以前的场地,但内容是迷笛的好几倍。”但这些“内容”也将摩登账上的一百多万烧光了。此后国内音乐节遍地开花,高峰期一年两百多个。而摩登天空音乐节和草莓音乐节则是绝对的头部。独音唱片的老板郭诚曾说,“自2007年摩登举办第一届音乐节开始,中国80%的乐队应该感谢沈黎晖。经历过来的乐队应该都清楚,是他让大家有了更客观的收入。”音乐节为独立音乐人创造了输出渠道,完成了音乐工业体系的最后一步,使之成为闭环。更重要的是,沈黎晖明确这是一个商业行为,他按照演出乐队带来的市场价值付费,终结了此前乐队在音乐节上“免费”演出的境况。现在乐队也可以根据市场行情进行议价。那次音乐节颠覆了很多传统——比如让刚出了一张专辑的国内新乐队重塑雕像的权利压轴;摒弃了请国外经典老牌乐队的传统,转而选择了正当红的新乐队Yeah Yeah Yeahs。一切都既大胆又新鲜。如彭磊所言,沈黎晖的世界观就是时髦,“他一直就是要新的,做之前的人没有经验做的事。”2017年摩登天空在英国利物浦开了分公司,甚至将音乐节也输出到了国外。在10月30日的发布会上,沈黎晖说,曾有4组摩登天空的艺术家登上英国独立音乐榜的Top50。 反无聊生产力沈黎晖有一种反无聊生产力,而这种能力成为了推动独立音乐向前进的核心能量源。当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街面上还满是穿着蓝灰色粗布工装的行人时,一条牛仔裤的出现点亮了沈黎晖,小朋友沈黎晖想,“会不会有一天大家都穿成这样?”他希望有个场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穿着很符合自身气质的衣服,而不是成为一只无聊的“蓝蚂蚁”。创作“奇怪”音乐的重塑乐队是“穿着牛仔裤的人”;嘻哈之于摇滚也是“穿着牛仔裤的人”;摩登旗下的视觉厂牌MVM是,他们参与设计的酒店也是……后来他看到了国外乐队的巡演大篷车,一个更时髦的“牛仔裤”,这个国内没有,沈黎晖想做,惊人的执著下,每来一个新人,沈黎晖就把这个任务派给他,直到痛仰乐队的经纪人把这事儿做成了。但因为国内的道路法规,改装后的大巴车只能坐四个人,装下一个乐队,连司机的位置都没有,还得派个车跟着,只有两个乐队将他的想法付诸实际,因为使用效率低下,这辆承载着沈黎晖梦想的大篷车还是在去年被卖了。
反无聊生产力沈黎晖有一种反无聊生产力,而这种能力成为了推动独立音乐向前进的核心能量源。当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街面上还满是穿着蓝灰色粗布工装的行人时,一条牛仔裤的出现点亮了沈黎晖,小朋友沈黎晖想,“会不会有一天大家都穿成这样?”他希望有个场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穿着很符合自身气质的衣服,而不是成为一只无聊的“蓝蚂蚁”。创作“奇怪”音乐的重塑乐队是“穿着牛仔裤的人”;嘻哈之于摇滚也是“穿着牛仔裤的人”;摩登旗下的视觉厂牌MVM是,他们参与设计的酒店也是……后来他看到了国外乐队的巡演大篷车,一个更时髦的“牛仔裤”,这个国内没有,沈黎晖想做,惊人的执著下,每来一个新人,沈黎晖就把这个任务派给他,直到痛仰乐队的经纪人把这事儿做成了。但因为国内的道路法规,改装后的大巴车只能坐四个人,装下一个乐队,连司机的位置都没有,还得派个车跟着,只有两个乐队将他的想法付诸实际,因为使用效率低下,这辆承载着沈黎晖梦想的大篷车还是在去年被卖了。 成立22年的摩登天空走到了新的赛段,他可以运用商业手段重新扶植自己的兴趣,但这种为兴趣买单的花费每年被限制在公司支出的20%以内。今年,沈黎晖用这笔钱投资了费那奇北京动画周,说独立音乐的体量也终于可以帮到独立动漫。在台上发言时,曾经的摇滚明星变得羞涩,空荡的左手在身侧上下摩擦,试图寻找藏在长外套下的口袋。沈黎晖觉得那些做独立动漫的人都异常纯粹,像是小白兔,而站在台上摩擦衣服的自己则是个“坏人”,“我想法特别多,这事儿怎么赚钱,这个阶段怎么实现什么目标,想得一清二楚你知道吗?”沈黎晖不指望这些投资挣钱,至少短期内不指望,他看重的是文化价值,比如他还给一些民族乐曲出片。但投资人不行,他们需要回报,需要财报好看,等不了沈黎晖那些所谓的长期价值,“那就得把我们所有不赚钱的项目砍掉,报表就好看,但是你的长期竞争力,门槛还是不够高。”沈黎晖不愿意,所以每当有新的投资人想进来时,他都会问“你是不是要求我们上市?说是,我说你不能写这种要求,他说那我们就不投嘛。好。”沈黎晖觉得当把上市作为目标,企业行为就会走样。于是他进行股权的回购和解,把70%的股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做自己的主。对于财富,沈黎晖没什么欲望,那些代表所谓有钱的行为,沈黎晖都没兴趣。“你买个车算什么,买个房子,弄个别墅算什么,你开一摩登天空才证明你有钱,因为这事儿多烧钱对吧?看起来这么不靠谱一事儿,能干20年我觉得这才是最奢侈的事。”沈黎晖身上有一股遮掩不住的少年心气,它们大多从他被法令纹拢住的嘴角流出来。也许是音乐也许是更加新鲜的事物,这些总能为他提供情绪的欢愉与饱满,一直像个少年。现在,音乐工业系统在摩登天空已经跑通,且顺畅地运转着,沈黎晖进入后摩登时代,他现在希望摩登天空看起来不太像一个音乐公司,他总是在甩脱标签,因为无聊,他不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公司被定义,“我们总想让自己看起来怪一点。”
成立22年的摩登天空走到了新的赛段,他可以运用商业手段重新扶植自己的兴趣,但这种为兴趣买单的花费每年被限制在公司支出的20%以内。今年,沈黎晖用这笔钱投资了费那奇北京动画周,说独立音乐的体量也终于可以帮到独立动漫。在台上发言时,曾经的摇滚明星变得羞涩,空荡的左手在身侧上下摩擦,试图寻找藏在长外套下的口袋。沈黎晖觉得那些做独立动漫的人都异常纯粹,像是小白兔,而站在台上摩擦衣服的自己则是个“坏人”,“我想法特别多,这事儿怎么赚钱,这个阶段怎么实现什么目标,想得一清二楚你知道吗?”沈黎晖不指望这些投资挣钱,至少短期内不指望,他看重的是文化价值,比如他还给一些民族乐曲出片。但投资人不行,他们需要回报,需要财报好看,等不了沈黎晖那些所谓的长期价值,“那就得把我们所有不赚钱的项目砍掉,报表就好看,但是你的长期竞争力,门槛还是不够高。”沈黎晖不愿意,所以每当有新的投资人想进来时,他都会问“你是不是要求我们上市?说是,我说你不能写这种要求,他说那我们就不投嘛。好。”沈黎晖觉得当把上市作为目标,企业行为就会走样。于是他进行股权的回购和解,把70%的股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做自己的主。对于财富,沈黎晖没什么欲望,那些代表所谓有钱的行为,沈黎晖都没兴趣。“你买个车算什么,买个房子,弄个别墅算什么,你开一摩登天空才证明你有钱,因为这事儿多烧钱对吧?看起来这么不靠谱一事儿,能干20年我觉得这才是最奢侈的事。”沈黎晖身上有一股遮掩不住的少年心气,它们大多从他被法令纹拢住的嘴角流出来。也许是音乐也许是更加新鲜的事物,这些总能为他提供情绪的欢愉与饱满,一直像个少年。现在,音乐工业系统在摩登天空已经跑通,且顺畅地运转着,沈黎晖进入后摩登时代,他现在希望摩登天空看起来不太像一个音乐公司,他总是在甩脱标签,因为无聊,他不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公司被定义,“我们总想让自己看起来怪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