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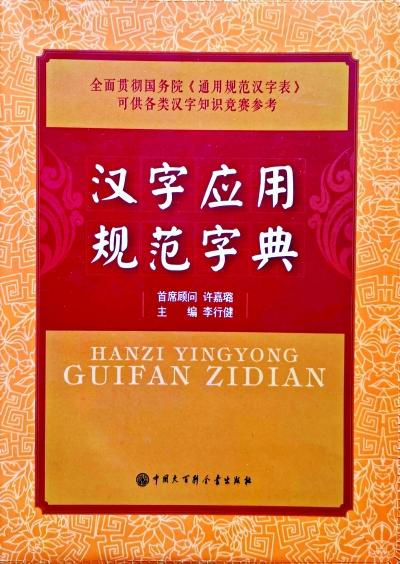

董旭东 绘

语言学家曹先擢、吕叔湘、李行健(从左至右)。

贾镇歌
2019年12月20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与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2019”在京揭晓——“稳”“难”分别当选年度国内字、国际字;入围的一批网络新词“硬核”“断舍离”反映了当下社会生活的新现象和新变化。互联网时代,新词迭出,原也正常,可业内人士却直陈,当下汉语语言文字的应用,面临“粗鄙化、游戏化”危机。
无规矩不成方圆。他是编写现代汉语言文字规范辞书当之无愧的方家,在60年的专业生涯中潜心学术,历时11年主编完成《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虽然在语言学界之外,他的名字鲜为人知,但很多人的案头都离不开他编写的工具丛书,堪称“最熟悉的陌生人”。他就是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辞书学会顾问,85岁高龄的李行健。
正如他在汉语词典的前言中所述:“大家参加这项工作不是为了获取什么,而是希望为国家的语言规范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总能不断克服前进中的各种困难”,他希望今天的年轻读者更好地珍视自己的母语,因为它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而规范运用是珍视的基础。”
1
险些与语言学擦肩而过
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满眼全是书籍,地上也有好几堆书,唯一没有为书籍挤占的空间,就是一把办公椅了。李行健的办公室,既是一方小天地,也是他的大世界。
“其实我最初的理想不是研究语文,各种阴错阳差,语言学倒陪伴了一生……”
李行健1951年初中毕业后,不忘当时班主任对于他们的嘱托:“国家穷,就是因为不会造飞机和汽车,不会生产先进的武器,唯有工业救国。”老师鼓励他报考重庆的西南工业专科学校(后并入重庆大学)。
在专科学校学习与进工厂的实践过程中,他突然萌生一个念头,想去当新闻记者,发挥“上传下达”的作用。1952年,正逢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由北大、清华、燕京等著名高校中文系合并成新的北大中文系,在当时造就了“众星云集”的盛况,王力、游国恩、魏建功、杨晦、高名凯、周祖谟等等知名学者汇聚于此。次年,北大还从城内沙滩红楼搬到了西郊燕园。“一是因为北大浓厚学术氛围的诱惑,再有就是理想的转变,成天幻想做‘人民的代言人’,报考了北大中文系的新闻专业。”时隔半个多世纪,李行健说起往事依然激动不已,双手不时在空中划出几道弧线。那年9月,李行健顺利考入北京大学。
恰在这入学的当口,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劝他改学文学专业。“新闻专业更倾向于有社会经验并且年龄偏大的调干生,我们这些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学生,就听从安排去了文学专业。”
愉快服从国家的需要,也使他迈向了学术生涯的第一步。他在北京大学学习的第3年,系里对专业进行了细分,一部分同学攻读语言学,一部分学习文学。那时中文系的学生大都觉得语言学是一门枯燥的学问,而文学专业仿佛更加浪漫有趣,其中一位被分配到学习语言的同学,终日愁眉不展,茶饭不思。由于当时计划性很强,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能随意变动名额。看到这样的情景,他做出了一个人生中重要的抉择,主动要求替换那名学生学习语言学。还有一个缘由是,任教“语言学引论”的高名凯先生坚持自己学术观点的勇气与亲切自然的人格魅力深深打动了他:“我能终身从事语文工作,同他有密切关系。”
如今回望过往,他说自己选择语言学作为终身事业“非常正确”。语言学这门极具魅力而又充满挑战的学科,与他的人生轨迹重合在了一起。
2
未名湖畔五年“三部曲”
从1953年入学到1958年毕业,5年的光阴影像刻在了李行健记忆中。在这里发生的三段故事如同他初涉人生的“三部曲”。
第一个故事,“雪中送炭”。
1953年底,李行健查出得了肺结核,按规定只能休学。由于家远在四川,经济状况也比较困难,他渴望留在学校一边治疗一边学习。当时学校内部的治疗康复中心名额有限,不批准他去那里休养,甚至提出限时离校,停止供给助学金。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找时任系主任杨晦先生表达诉求。他至今记得恩师当年的一番话:“今天是人民的国家,你们有困难,我会尽我力量去帮你们解决。”在杨先生的帮助下,李行健终于留在了北大,一边治疗一边学习。杨晦先生不仅对学生关爱备至,更是知识广博有见地的学者,他坚持倡导“语言和文学有机联系”论:学习语言学的同学也要学好文学,学习文学的同学也要学好语言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学是重要的基础,这正是中文系的两根支柱。
第二个故事,“意料之外”。
一次春节联欢中,李行健正好坐在享誉中外的著名文学史家、楚辞学专家游国恩教授旁边,闲谈中他问起了李行健的家乡,得知李是遂宁人。
后来的一次古代文学期中考试,主考官正是游教授。当时的考试是口试作答,抽签决定题目,有半个小时的准备时间。李行健准备充分,口试的过程较为顺畅。突然,游教授说:“李行健,我还要考你一道题。你不是四川遂宁人吗?遂宁同《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吗?”
“突然听到这个问题我就可劲儿想,灵光一现,想到了家乡遂宁有一个诗人叫张船山,他的妹妹嫁给了高鹗,而高鹗传说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书人。”李行健回忆,当时也不知道自己说得对不对,看到游教授脸上露出的微笑,心里踏实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李行健一直珍藏着一本记分册,里面有游教授给他写上的一个“优”字。老师对每一位学生的观察都细致入微,随口就可以说出学生的籍贯,并快速同考题融合在一起,一方面体现了对学生的关心,另一方面充分展现了游国恩教授的博闻强识、学养深厚。
第三个故事,李行健命名为“独立思考”。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奠基人魏建功,家里藏书甚多,很多重要的书籍还都存下一个副本,目的之一是为方便学生借阅。
一次李行健对《论语》中的一句话不太理解,就去请教魏教授。“魏教授问我查过《辞海》等工具书没有,我说并没有查阅,魏老师脸上顿时露出了不悦之色。魏教授说,读书要用工具书,遇到问题要先查工具书,这样才能培养起自学能力,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今天我不回答你的问题,等你查完工具书后再来找我。”
从那以后,李行健更清楚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道理。大学教育应该培养学生独立钻研的能力,进而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北大精神到底是什么?就是与时俱进、独立思考、不迷信、不盲从。”
听他的讲述,如同看老电影,那些知名学人的音容历历在目。他说,自己在北大学习的5年,寒暑假从没回过老家——假期正是图书馆有座位又方便借书的时候,也是向老师请教的好机会。他特别怀念那个埋头读书的年代。
3
完成吕叔湘先生未竟的事业
李行健毕业那年,国内各省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分院。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报到的时候,语文所就我一个人。”
那时,语言学大师吕叔湘提出了结合地方特色,搞河北省的方言调查。由吕叔湘、丁树声先生提议,河北省的方言调查落在了李行健一人的肩上。要对百十个县展开方言词汇调查谈何容易,于是他动员当地语文老师一起参与调查活动。“有一年基本都是在河北省的县里面走动,既要指导那些老师,还要整合繁杂的资料。”
1962年起,李行健调入天津师范大学,担任教学工作,并担任《天津师大学报》负责人多年。直到1983年,他被调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那年国务院下文让当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为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作科学的研究,作为今后决策的依据。
研究所成立之初,缺少人手,研究所有三个从外地调人的名额,条件是50岁以下,有高级职称,具有学术研究的能力。经吕叔湘推荐,李行健偕全家由天津来到北京,参加筹备成立研究所。工作步入正轨不久,他又被任命为语文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协助时任社长吕叔湘工作。
语文出版社成立前,只有文字改革出版社,但由于社名和出书的限制,并不能适应语言学事业发展的需要。吕叔湘先生同叶圣陶、胡愈之、张志公、金灿然等先生多次研究后,决定要设立一个为语言学出书的专门的出版社。这样,在原来的文字改革出版社的基础上,建立了语文出版社。李行健写过好几篇文章,谈到吕叔湘先生已经人到晚年,很多社会工作都辞掉了,依旧在语文出版社任社长,目的就是要多出一些语言学方面的好书,解决语言学出书困难的问题。
1987年,李行健对当时市场上的语文工具书进行了一番调查,并根据读者的意见以及语文出版社的自身特点,提出了想要编写一部规范词典的设想,为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服务。
1988年,在中日友好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他被日本文部省聘请,任教于日本最著名的十所大学之一的国立一桥大学。在两年半的时光中,他经常去日本的书店,发现那里的工具书包罗万象,非常全面,连公交出行都有专门的工具书可查。看到日本出版的词典形式多样,种类丰富,他深有感触,特意就此事给吕叔湘先生写了一封长信。他想要编写一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1992年春,在吕叔湘、许嘉璐、曹先擢、柳斌等先生的指导下,成立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委会”,由李行健主持具体工作。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编写规范词典列入“八五”工作规划当中。李行健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前言中说道:“从正式编写到完稿经历了12年,编写组在一无编制,二无国家拨款的情况下,全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坚持编写工作。主要人员是离退休的老同志,他们工作认真,态度严谨。现今有的同志已经去世,前后有几位副主编积劳成疾,无法再坚持工作。”他们在离退休的年龄,本来可以安度晚年,但是他们为了汉语言事业献出了每一分力。
1998年1月,吕先生已经病重,《现代规范汉语词典》还未出版,李行健拿着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字头汇编成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的样书去看望吕先生。吕先生笑笑说:“希望词典也尽快出版。”
2004年,新书出版,第一个月全国销量就高达10万册。“吕叔湘先生虽然最后没有能够亲眼看到《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出版,但他若泉下有知,也一定会高兴的。”
4
再为汉语国际化做点事
2009年,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发起一项倡议,由两岸一起编写一部《中华语文大辞典》。大陆一方决定交由《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组完成这一任务。
原来,在此之前发生过一件令人笑不起来的小插曲——在两岸交流会上,台湾方面的负责人对大陆给予赞美之词,可能是为了活跃气氛吧,套用了一句台湾的口语:“我感到忒窝心了”。会场上的人顿时面面相觑,气氛尴尬。“窝心”在北京话中指的是不开心,表达苦闷之意,而台湾那边的意思却正好相反,说的是舒心。“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语言是连接海峡两岸的重要纽带,我们拥有同一母语,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两地语言的差异分歧着实不少。”李行健将之概括为“一语两话”“一文两体”。“编写一套沟通海峡两岸中国人都看得懂的词典何其重要!”
从2010年3月,两岸在北京召开合编《中华语文大辞典》的协商会算起,经过整整6年时间,先后出版了《两岸常用词典》《两岸通用词典》,增收词条达到了10万条左右,拟再增收词条到15万条,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华语文大辞典》。两岸合作编写辞典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李行健粗略统计了下,编写组在过去20多年里,共计出版了30多部词典,编写的词典两次获得国家图书奖,他个人也摘得辞书终身成就奖。
这些年始终有一件事情让李行健和他的编写团队放心不下,那就是汉语的国际推广问题。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提出过:“现代人都学习英语、日语、德语、俄语、法语,今后可以预计,很多人要学习汉语。学习英语有《牛津英语大词典》等各式各样的学习语言的词典,那我们汉语有没有一本这样的词典供外国人学习我们的汉语呢?我们应该做这个工作。”这件事情一直放在李行健的心里,即便年逾八旬依旧站在教学岗位的第一线。“再为汉语国际化的工作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就可以真正退休了。”
互联网是当今社会最鲜活的汉语应用场景。不过,由于每个人的文化修为、认知水平不尽相同,网络语言难免鱼龙混杂。虽然平素上网无多,李行健一直对网络流行语持开放态度。“语言文字规范从来都处于动态调整之中。从语言发展的趋势来看,一些曾经被视作不规范的用法后来也慢慢被使用者接受认可,网络语言也有部分最终会沉淀下来。”他建议,在规范化使用汉语,抵制低俗语言层面,教科书、主流媒体要带头示范,引导汉语规范的发展植根于良性土壤。


